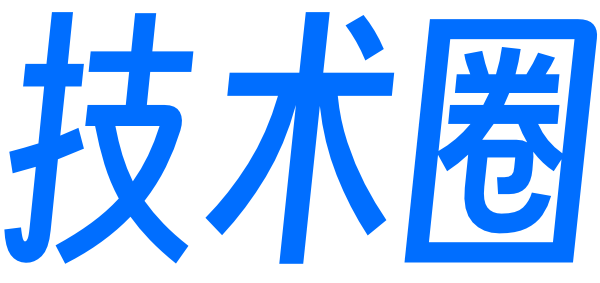项飙:“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有劳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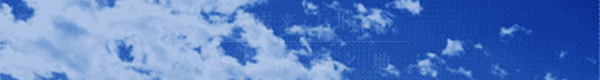

自认为“不了解”科技行业的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向科技界提出了三个问题。他从三个带有人文关怀的视角对科技发展进行了思考:什么是系统?谁被困在系统中?“困”字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
本文为项飙先生在1月9日“腾讯科技向善暨数字未来大会2021”上的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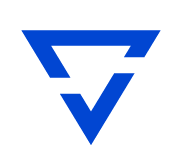

计算下面有算计。但当系统通过一个计算的方式建立之后,好像算计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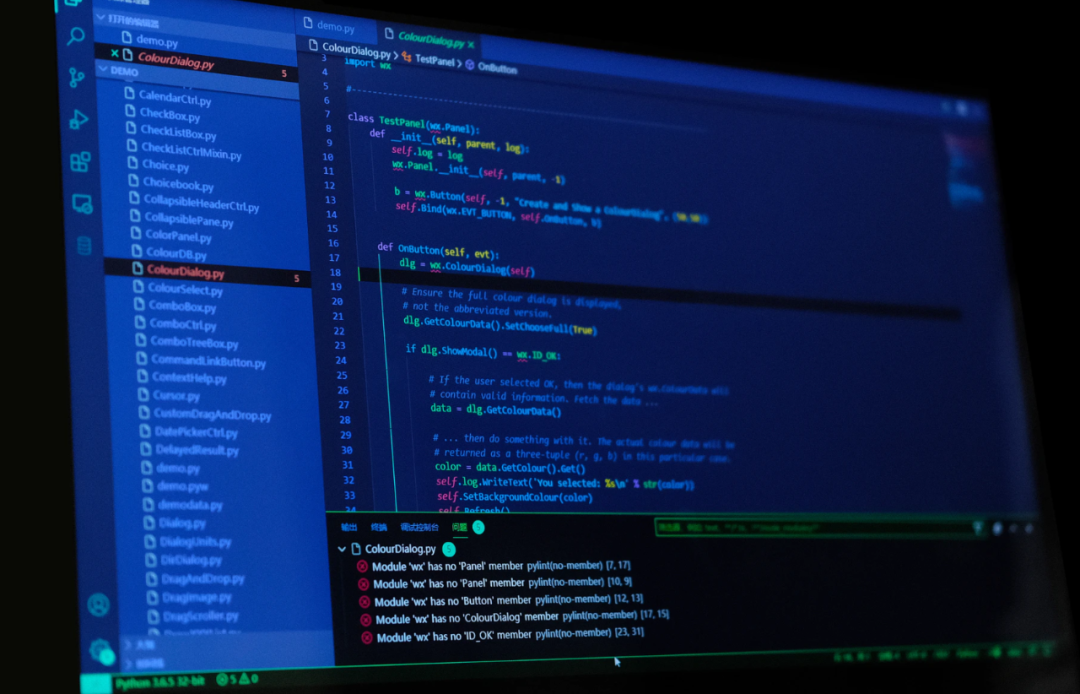
他们困在系统里面,工作状况被系统所控制,感到很强的受挤压感、被压迫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跟19世纪拉美地区甘蔗园的工人没有太大差别。

点外卖带来的“慵懒”其实并不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感,但是整个社会为这份慵懒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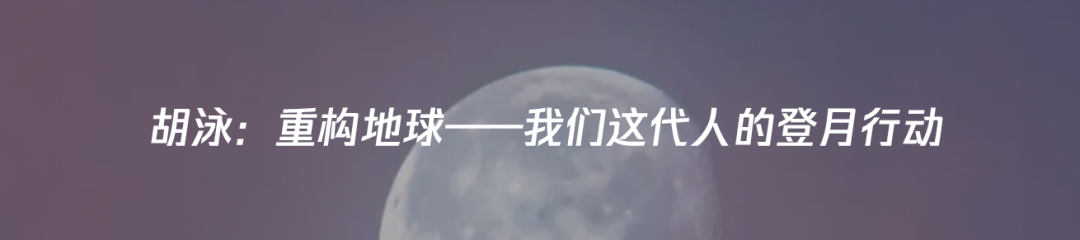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