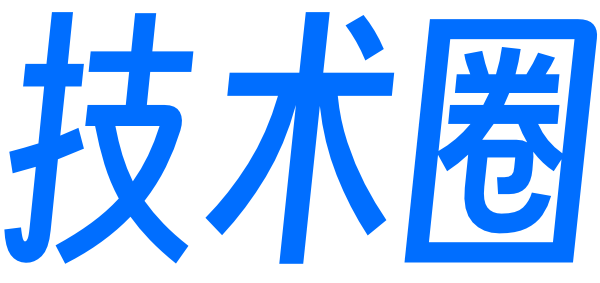上海,给我多巴胺;襄阳,给我内啡肽
辞职后驾车去襄阳待了一周。
这短短几天在襄阳的时间,一次次激起我对在上海生活的反思,因为它们带给我的感受太不一样了。
襄阳作为一座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出名的城市,时间好像从来没在这里被切断成一块一块的,时间借由古老的城墙一分一秒不急不躁走到今天。
古城墙在襄阳不被叫做遗址,它依然名正言顺的占据最繁华的地段,和来来往往的行人互动;它依然参与着今天人们的生活,人们在城墙上看日出日落,在城根下闲谈垂钓;它依然守护着这一方水土,经过一代代人的修补,它看起来还是那么稳固,沉稳安静的青灰色砖块守护着这座城市。
如果你抚摸过这些砖块,一定会欣喜地发现那一刻与历史的连通。
城墙在襄阳没有老去,它继续与这里的人们一起呼吸,见证历史包容历史,从不多说什么,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襄阳还有一种魅力源于这里的人和生活。
或许是有浓厚的历史作为气质中最深沉的底蕴,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有着非常明显的属于自己的自信和节奏。
和这座城市一样,这里的人们深知他们血液里记忆里带着不曾中断的文化的积累,所以,他们有和前人一样的韧性与努力,但又不执着于欲望与贪念,热情地生活,勤奋地劳作。
这块土地的自然条件如此和谐,在崇山峻岭中的一小块平坦的土地,拥有优渥的水利条件,就连首尔的汉江也是参考襄阳的城市规划而建;一年到头气温适宜,农作物可以一批批更迭生长,有人们也随着忙碌磨去了骨子里的懒惰;深居内陆之中,周围被复杂地形隔绝开来,很难被外邦的文化侵扰,撑起形成了特别的属于襄阳的气质——踏实、热情、懂得满足。
在襄阳待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人们很有自己的一套平稳的节奏,新鲜事物任它来,但如果不符合襄阳人的节奏和喜好,很快就会被淘汰。
在这里,快乐能够被自己生产:在平稳的汉江里游它几个来回;天黑后在江边夜钓;小龙虾烧烤片片鱼半夜才正式进入状态;永远别担心喝酒回不了家,代驾会温暖又热情地守着你。
在汉江边和古城墙下,我拥有了一种平稳踏实缓慢的快乐。
回到上海,我以为这里有被保护得很好的古建筑,可是在去过一两次之后,就失去了兴趣。
那些一条条说是充满上海风情的老街,入驻了一个又一个新式的、外国风情的洋玩意儿,这些地方已经没有上海人的生活与文化了。
它们与上海,被强行编织在一起,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离奇的景象:在曾经英租界的法国梧桐树下走进一家日式咖啡店喝一杯意式浓缩,看每一个路人都精心打扮成演员模样,用奇装异服等待老法师的长枪短炮。
如此这般让人混乱的元素妆点着这座城市,让我已经无法找全她历史的片段,更无从下手将这些片段串联。
在上海,时间和历史被切割了,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变成了特定时期的上海——民国时的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等等。可是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呢?吴侬软语的姑娘,小桥流水的人家无迹可寻,以至于有时会让我恍惚它们不曾存在。
而在上海的这些年,于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多巴胺制造机,像一个巨大的赌场,人们带着对赢的欲望走进金碧辉煌的所谓的人间天堂,挥金如土,每一场游戏都拥有无与伦比的新奇与刺激,让人们陷入疯狂。
那些原本可以自然而然收获的快乐被设计成一个又一个充满噱头的活动,比如看书、郊游、运动,在这里被打造成书店节、露营和飞盘,连愉悦放松的活动都变成经过设计、需要花钱、还要接受各种鄙视链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获取多巴胺的活动。这一切让我开始感到害怕。
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上海,仿佛有着这样一种循环:996赚钱、只会对着电脑动脑其实丢失了动手中获得的智慧与快乐、用为数不多的工资去购买各种被设计好的多巴胺的快乐、去努力融入一些需要入场券的圈子,这一切足够让工资所剩无几,如此一来就又要去乖乖搬砖,毕竟多巴胺的快乐让人成瘾难以戒断,而这些快乐又需要真金白银的购买。
在这个循环里的我,特别像一只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被放进轮子里不停奔跑,跑得好跑得快,就会被电击一下分泌多巴胺的大脑部位,如此刺激令我多巴胺成瘾,希望一直被刺激,于是我就需要不停地使劲地奔跑以此获得更多多巴胺式的快乐。
直到有一天力竭,停下来的一刻要么累死,要么因为缺少多巴胺的快乐而被比死亡还可怕的空虚所包围,这空虚不得不让我再次奔跑获得刺激。
所以,从襄阳回到的上海的第二天早晨,我一度陷入失落,在襄阳的快乐消失了,冷静后回想,那是襄阳制造的内啡肽的快乐给了我长久而平稳的满足。
又或者,这不是城市给予我多巴胺还是内啡肽,这是我自己是否清楚究竟是需要一个个接连不断的多巴胺的快乐,还是长久而平稳的内啡肽的满足。
我喜欢这世界,也喜欢它给我的反馈,我将长久地在这世界行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