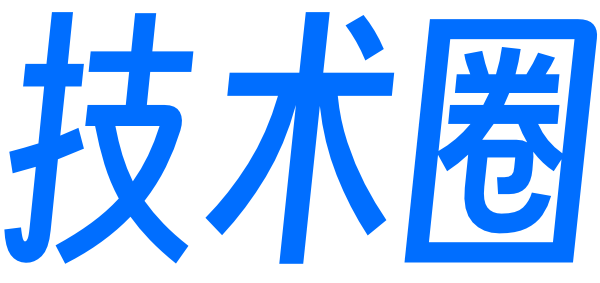危机应对指南:如何用理性打败“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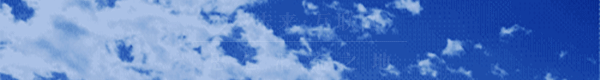

“承认危机,回归理性,而不是竖一个靶子,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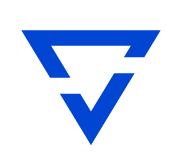

剧变
《剧变》探讨了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分辨危机、应对危机,避免危机,化危机为机遇,实现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剧变,是人类当下面临的主课题。
01
超越危机,全靠这十二手

接受现实。受创者常想:“如果没有这次意外,该多好。”这是康复的障碍。
承担责任。受创者易落入怨天尤人的陷阱中,指责命运、他人、社会等不公,从自怜中获得安慰,扭曲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划清界限。帮助受创者意识到:“确实出现了危机,但其他方面是正常的。”
向外界寻求帮助。
借鉴他人处理危机的方法。
自我力量。
诚实的自我评估。
参考曾经应对危机的经验。
耐心。
灵活的个性。
个人核心价值观。
不受约束。
02
所有国家都会走向历史的必然性

03
解决危机的方式,会塑造国家未来

04
美国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智利?

--------------- 往期回顾 --------------
喜欢本文?快点亮右下角“在看”吧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