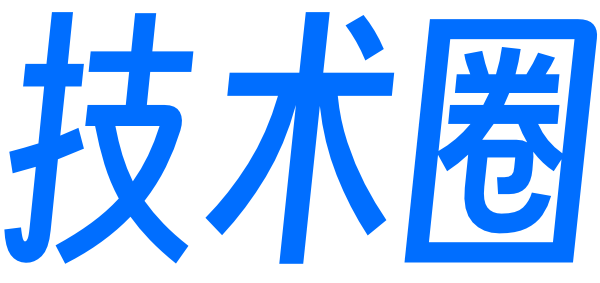泡泡玛特火了,可潮玩行业却“慌乱”了


全文5386字,阅读约需11分钟
文 | 浅蝉
来源 | 品玩
ID:pinwancool
泡泡玛特在2020年底一飞冲天,让整个潮玩行业出了圈。但跟着到来的,却是动荡。
随着关注度的提升和资本的涌入,潮玩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开始面对更多的诱惑,更大的焦虑以及更不确定的产业环境。原本风平浪静的“小圈子”,玩法和逻辑都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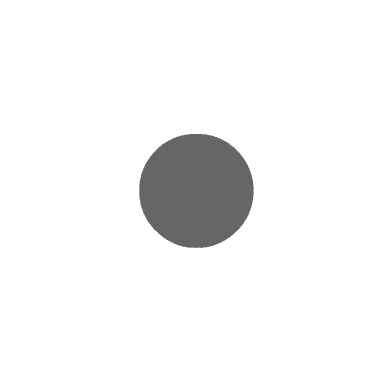
工厂跟不上了
潮玩本是一个小圈子的生意。诸多个人设计师品牌服务着自己的一小群拥趸,这样的“小本买卖”本是常态。但2020年12月泡泡玛特的上市,让许多原本不关注这个市场的玩家,开始想要进来分一杯羹。
从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来看,泡泡玛特的吸金能力无疑非常出众。2017年至2019年期间,该公司的营收分别为1.58亿元、5.15亿元和16.83亿元,同比增长率均超过200%;净利润则分别为156万元、9952万元、4.51亿,增长速度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毛利率也从2017年的47.6%上升至64.8%。去年12月11日泡泡玛特上市后,该公司的市值一路飙升,一度突破1100亿港元。
外界由此认准了一件事:成年人也需要玩具,并且由于他们的消费能力更高,这项生意只会比传统的儿童玩具更挣钱。
首先挤进来的,自然是资本。
伍超是一名潮玩设计师,也是潮玩品牌“超物”的主理人。前不久,一家想要进军潮玩圈的互联网巨头向他和多个设计师抛来橄榄枝,希望能收购他们的潮玩IP。
“1500万,换一个IP。”这是这家巨头给伍超的一个设计师朋友开出的价码。巨头看上了这个IP广泛的受众群,不过也提出要和设计师签对赌协议。
“你说我朋友是卖还是不卖呢?”伍超觉得,在巨额金钱的诱惑下,可能很少有人能直截了当地拒绝。
就像每一个被上市或者其他事件证明了潜力的“赛道”一样,许多投资者希望进入潮玩行业分一杯羹。但苦于缺乏前期积累,他们手里既没有成熟的设计师也没有优质IP,这时候砸钱往往是个万能的办法——圈外资本先重金买下一些独立IP,放到自己的品牌下生产,希望借此打出知名度,在圈内开拓市场。
根据伍超的介绍,向他们提出收购的这家互联网巨头,仅去年年底就迅速接触了十多家独立品牌,洽谈合作。效率一如既往地高。
这家互联网巨头对潮玩行业的垂青并不是个例。近一两年内,优酷、腾讯、B站等泛娱乐互联网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潮玩产品或包含潮玩元素的节目,去年10月已在纽交所上市的名创优品也通过独立新品牌TOP TOY入局潮玩行业。此外据报道,红杉资本、创业工场等10多家基金公司也正在加速布局潮玩市场。
咨询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称,中国潮流玩具零售的市场规模由2015年的63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207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34.6%,同时由于潮玩受欢迎程度的不断加深,预计2024年的市场规模将达到763亿元,自2019年起的复合年增长率为29.8%。
作为从业者,伍超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比较乐观。在他看来,潮玩的发展受地域、场地或其他常规行业因素的限制较小,同时已经在一定范围的年轻人中建立起了消费习惯。泡泡玛特能够在疫情严重的2020年逆流上市,也给他带来了不少信心。
潮玩的机会的确很多。但这种热闹终究是属于少数设计师的,对于构成潮玩这个生意的主体——大量的独立设计师来说,这些热闹带来的更多是一种干扰。
在资本看好后,越来越多原本并非潮玩圈子的设计师,也开始转做潮玩产品。首先被冲击的就是生产流程——工厂开始爆单。
“两三年前玩具生产工厂接不到足够的订单,因此会在潮玩展等场合主动给设计师发名片,希望能寻觅到合作的机会。但是最近设计师乌泱乌泱地往圈里进,厂家已经不缺单了,相反他们开始挑单。有时候他们即使接了你的订单,也会因为忙不过来而延迟交货。”独立潮玩设计师葱叔对品玩表示。

葱叔个人品牌Shining Daft旗下的一款潮玩(受访者供图)
他的订单就曾被厂家拖延过,“比如厂家答应二月交货,但是到了二月还没做出来,导致我也只能延期销售”。
而对于那些以预售为主的设计师而言,工厂生产延期导致那些已经付了定金的玩家迟迟收不到货,于是他们只得时不时地催促设计师。“我们对这些事情真的很头疼。”
在国内,90%以上的潮玩生产工厂都集中在广东东莞,不论是泡泡玛特这样的大公司,还是像葱叔、伍超这样的独立设计师,他们在完成了潮玩形象的设计、3D建模之后,都得把订单交给东莞的工厂进行生产。也因此,东莞的工厂们密切反映着潮玩行业的热度。
伍超也观察到了相同的现象:大概从2020年开始,他能明显感觉到行业内的订单量开始超出工厂的产能。最开始工厂毫不挑拣,有单就接。现在工厂不缺单了,就开始按优先级承接订单。他也经历过被拒单,因此要花很多时间跟工厂沟通。目前与他有长期合作的工厂稳定在5家左右,其中2家承担大部分的订单。

工厂中刚生产出来的潮玩单品(受访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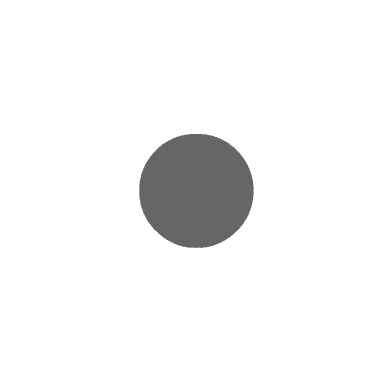
盲盒,盲盒,还是盲盒
行业骤然起飞带来了混乱和无序,不仅冲击了生产流程,还深刻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喜好”——由于泡泡玛特主打盲盒产品,导致无论是新进入的玩家还是焦虑的老玩家,都重点打起了盲盒的主意。
盲盒通常以系列的形式进行设计和销售,同系列中不同的设计被设计师们称为“形象”。
它的游戏机制正是在于一个“盲”字,即玩家在购买某个盲盒时,只知道其所属的系列但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款形象——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买小浣熊干脆面收集水浒卡,不过盲盒可比干脆面贵多了。
这种不确定性为玩家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同时也刺激着他们的购买欲。
“盲盒的一个系列里可能有‘6+2’或者‘8+2’个形象,多一些的可能是‘12+2’。意思是其中有6个、8个或12个常规形象,再分别加上两个隐藏款。”伍超介绍道。“隐藏款也有小隐藏和大隐藏之分:小隐藏的数量多一些,大隐藏相对少一些,例如一个系列里小隐藏被抽中的几率是五分之一,那么大隐藏被抽中的概率可能是十分之一。”
隐藏款可以说是玩家们的终极追求。为了得到它们,玩家们不得不各出奇招。
如果说单个购买盲盒是常规行为,那么升级版的操作则需要“钞能力”的加持。在盲盒玩家圈子里有一个术语叫端箱,意为把一整箱盲盒(通常为六到十二个)全部买下。
很多玩家最难以抵抗的就是这种一次性打开所有盲盒检验自己战利品的时刻。
“盲盒这种东西,要么不买,要么端箱。”小K在社交平台上的发言虽然略有些开玩笑的成分,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一部分玩家的心理。
盲盒“隔壁”的手办圈曾经有一句玩笑话,“手办一面墙,北京一套房”。盲盒的单价通常在59元到79元之间,固然不如很多手办昂贵,但以数量取胜。一次端箱可能会花费几百元,想要达成全系列甚至多系列齐全的成就,可能需要数千元。
资深盲盒玩家小尤曾在网上秀出了自己入坑一年来的全部收藏——几张照片上全是贴墙设置的盲盒玩偶陈列架,一眼望去甚至数不清玩偶的个数。据小尤自己统计,这些玩偶大概有1000多个,放眼望去非常震撼。像小尤一样几面墙都是盲盒玩偶,背后的花销可能已经达到几万之多。
对于不玩盲盒的人来说,这些钱可能花得并不值得。但是在那些玩家看来,钱都是自己挣的,他们就是愿意花钱买个开心。
伍超试着从玩家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行为,“这也许是一种精神刚需。就像我永远缺一本书,缺一场电影,每个月必须留有买书,或买电影票的预算。潮玩玩家每个月也会为钟爱的潮玩留有预算,现在这个习惯已经有了。”
品牌商家当然很喜欢这种趋势,在他们看来,盲盒门槛低、销量高,是非常适合盈利和开拓市场的一类产品。而泡泡玛特正是把这些特点发挥到极致的代表。
此前超物某一个系列的盲盒生产了7.2万个单体,目前正在制作中的系列盲盒有10万个。伍超的经验之谈是盲盒产品以五万单体以上的数量为佳。而泡泡玛特的盲盒生产、销售规模则翻了100多倍。据招股书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泡泡玛特总共卖出了1351万个盲盒,销售额6.89亿,占总营收的84%。
玩具生产的工业化流程是设计,3D建模,开模,打样,批量生产。像盲盒这样的产品可以大批量生产,其中的成本就能更多地分摊到每一个单体身上,降低平均成本,因此售价也可以控制在大众易于接受的区间内。
这种对盲盒的追捧,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盲盒设计越来越明显的同质化问题。

“可以看到目前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盲盒玩偶形象是人形小女孩”,入行已有四年的葱叔总结道,“这种形象符合盲盒的主要消费群体——年轻女性——的审美需求。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的Molly系列就是很好的例子。”
照着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盲盒形象可能会火爆一时,但难以支撑整个品牌的长期发展。伍超对此还算清醒:“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期行业里的泡沫很多,诱惑很多,作为主理人最重要是明白自己要做的是什么。观众喜新厌旧速度越来越快,这也是对设计师的挑战——大众渴望新的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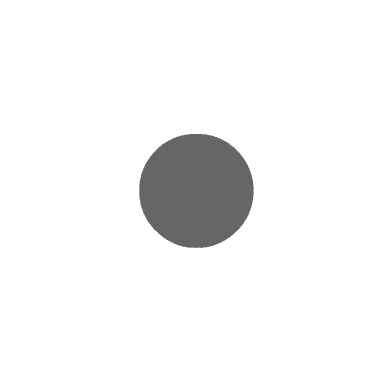
盲盒之外呢
而比同质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随着泡泡玛特的出圈,盲盒的销售机制受到了大量质疑。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抽盲盒带有一定的赌博性质,为了所谓隐藏款而大批量购入盲盒的行为也并不能算是理性消费。
去年年底,新华社曾出言评论盲盒营销,指出“盲盒热”所带来的上瘾和赌博心理正在滋生畸形消费,不少盲盒爱好者每月花费不菲。今年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也针对盲盒市场发布消费提示,要求经营者规范销售盲盒,同时也希望消费者不要盲目购买。
这些风险,以及同质化后越来越窄的增长空间,让许多品牌商家开始把眼光投向其他潮玩品类。
在大部分圈内人士看来,盲盒以外的产品可以被统称为大娃,而大娃又可以细化出很多不同的支线。
为了丰富产品线和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很多潮玩品牌都开始向大娃品类发力。泡泡玛特也不例外,它在招股书中将自己的潮玩产品线分为盲盒、手办、BJD(Ball-jointed Doll)及衍生品,而名创优品旗下新成立的潮玩品牌TOP TOY则直接将自己的潮玩产品分为八大品类:盲盒、手办、娃娃、合金、大众玩具、积木、拼装、雕像。
外界一直关心泡泡玛特是否会在盲盒以外的产品上发力,对此泡泡玛特合伙人司德的回应是:其实泡泡玛特每年会有上百款非盲盒类的产品推出来,比如BJD娃娃、十几公分到几十公分不等的手办。只不过这些产品的问题在于产量相对较少,卖得也比较快,大部分玩家可能没法在店里看到。
“我们在(大娃方面的)生产量方面可能太保守了,现在不缺营销推广,缺的是货量,供应没那么足。现在很痛苦的一件事是,泡泡玛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圈了,但是是靠盲盒破的。我们自己的粉丝知道我们有大号的玩具,但是大众其实是不知道的,我们未来可能要更努力地改变这件事。”
另一方面,从IP角度来讲,品牌粉丝可能会希望产品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泡泡玛特也在尝试推出一系列衍生品,比如挂件、徽章、毛绒玩偶等。
在泡泡玛特的淘宝旗舰店上,确实可以看到手办、BJD娃娃等产品,但月销几十、几百个相较于盲盒四位数的销售量而言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不久前成立的TOP TOY则采取了另一种模式:从一开始就不把重心完全放在盲盒上,而是将品牌定位为潮流集合店,用TOP TOY CEO孙元文的话说就是“做潮玩界的安卓系统”。
在发展路线的选择上两者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可以猜想TOP TOY走这条路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避免与已经具备一定知名度和市场份额的泡泡玛特同质化,二是开发潮玩市场在盲盒之外的深层潜力。
在孙元文的设想中,非盲盒类潮玩除了实际销售,还可以承担消费者拉新的重任。
对于一个崭新的品牌来说,如何打开品牌知名度是一个巨大的考验,TOP TOY选择在旗舰店里摆放一些大型非卖品潮玩,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网红景点来吸引玩家和路人打卡拍照,提升店内流量,同时也增加品牌在社交平台的曝光度。

TOP TOY梦工厂店中的Joker雕塑
“在梦工厂门店中,我们用三分之一的面积陈列稀缺款、绝版潮玩,就是给消费者看的,没有任何销售可言。我们一开始不需要顾客买东西,而是要让他们感受到潮玩文化的价值。”挖掘市场潜力的第一步就是培养和教育消费者,从这一点来说TOP TOY的策略是正确的。
不过回到商业价值方面,大娃似乎会为品牌的商业化带来一定的挑战。
从本质上来说,大娃比盲盒更偏向艺术品——所谓各花入各眼,更偏重设计感和独特性的大娃很难像盲盒一样广泛地迎合大众审美,因此只能在特定玩家群体中流行。
再从生产层面来看,每款大娃从设计图到实际生产之间需要经历开模的过程,其中的成本很高。ABS、PVC(两种比较常见的合成材料)玩具的模具一般是2-3万元一套,而一个大娃根据难易程度的不同需要做1-5套模具。
“普通盲盒玩偶体积较小,造型简单,通常做一套模具就足够了。而相对复杂一些的大娃,可能脑袋、身体、四肢、道具等部分都要单独做套模具。比如我们工作室目前正在生产的一款大娃,每个部位都是单独做的模具,其中钢模足有三套,搪胶模具有四套,总共七套,花费了十多万元。”
据伍超介绍,这款大娃计划第一批生产1000个,那么每个单体光是开模成本就有100多元,更别提还要加上其他生产、运输、营销成本。这样来看,最后将单体的销售价定为699元并非漫天要价。事实上,行业内还有很多定价高于699元的大娃,一些体积更大或更有设计感的大娃甚至达到数千元。

超物旗下的双骨猫-共生
虽然从成本和审美价值的角度来讲这些定价无可厚非,但是比盲盒高了十倍的价格似乎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并不友好。
因此大娃的种种特性决定了它们很难达成批量化的生产和销售,这似乎又给独立设计师们留下了一丝生存的空间——那些商业化大品牌如果想做大娃生意,要考虑的事情似乎还有很多。
但无论如何,潮玩这个生意已经无法回头地走上“大众化”的道路。无论是已经存在的独立设计师、大品牌,还是新加入的外来者,他们都在重新考量自己眼前的机会,毕竟潮玩这个行业从生产流程到商业模式的逻辑,都要彻底地改变了。
本文由品玩授权亿欧发布,申请文章授权请联系原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