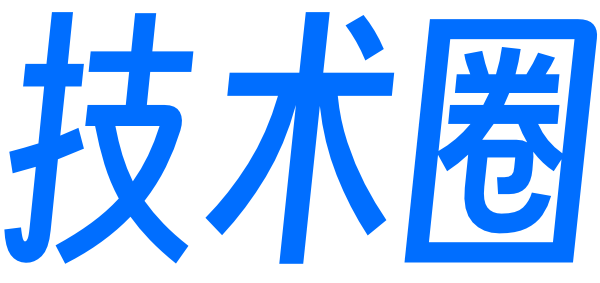游戏的特质:当我们说“play”的时候,究竟在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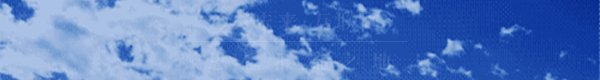

在中文语境中,说起“玩”,我们常常会产生“把玩”等联想;而在英文中,说到“play”时,又常常意味着比赛或演奏乐器。这些含义都与我们当下所说的“玩游戏”相去甚远。正因如此,随着游戏形态的不断演变,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play”的含义。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同时期发展的新媒介理论也开始重新讨论诸如数字信息时代电影或者戏剧等传统艺术。然而,伴随着20世纪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媒体通过数位编码和显像技术,这就是电子游戏。
电子游戏的媒介历史可以追溯到电子计算机技术诞生之初,然而当我们使用“电子游戏”这个中文词汇讨论这些媒体时,我们翻译并引用的英文原词应该是“Electronic Game”还是“Video Game”?
其实早在计算机还在开发的20世纪30年代,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已经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游戏的研究,而“游戏”与“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辨析的,赫伊津哈的著作《游戏的人》 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赫伊津哈总结出了游戏活动的三大特征:
游戏是自由的。游戏是非物质、非理性的行为,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它遵循自由参加的原则,受命参与的游戏就不再是游戏,最多只能算对游戏行为的模仿。
游戏有别于真实生活。游戏是暂时创造出一片完全由游戏规则支配的空间,每个参与游戏的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只是在假装”,或者说只是好玩而已。
游戏受限制。限制游戏进行的条件很多,比如必需有进行游戏的空间、游戏规则、需要在特定时刻终止等等。但因为游戏受限制、有自己的进程,决定了它是可重复的,能够形成文化和传统。几乎所有游戏都有重复或交替要素。
在此基础上,赫伊津哈给“游戏”这一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
游戏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一种自愿活动或消遣;遵循自愿接受但又有绝对约束力的原则,以自身为目的,伴随有紧张感、喜悦感,并意识到它不同于平常生活。
基于此定义,赫伊津哈开始据此分析游戏与文化的关系。而我们也可以对中文语言现象中的“游戏”与“玩”的具体用法进行研究。
在中文翻译为“玩”以及“玩家”的概念,其词源不是拉丁语的Ludus。中国传统意义的“玩”与“把玩”玉器有关,这里所指与我们要讨论的新媒体理论相距甚远,我们不展开讨论。
另一方面,在大量国内的新媒介理论中,对于“电子游戏”和“电子游戏玩家”的使用基本都是在借用“Play”这个词汇,以及其在英语中所指的范畴。可这一用法导致的问题恰恰在于,因为英语中“Play”与“Player”这个概念囊括的领域比拉丁语Ludere还广,所以“Play”的专门含义完全被“轻松的活动”和“运动”的含义掩盖(在日耳曼语族中显得更为明显)。
我们无法就“Play”所有能指的起源进行密集排查工作,而且现代汉语书写的媒介理论中“玩家”的概念虽然直接翻译来自英文“Player”,但具体到语境中使用也有很大的出入(比如Player也指竞赛运动员、乐器演奏家,但中文的“玩家”并没有对应的含义)。
所以,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有必要就“电子游戏”中“游戏活动”概念的使用环境展开具体的讨论。
01
对比:传统游戏与电子游戏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第一位提对“Play”一词定义的分析哲学家。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他认为游戏的要素,如游戏活动、游戏规则和游戏中的竞争,都不能充分定义游戏是什么。
维特根斯坦由此得出结论,人们将“游戏”一词应用于一系列不同的人类活动,而这些活动彼此之间只具有人们可能称之为家族相似性的东西。
家族相似性(德语:Familienähnlichkeit),即用同一个字代表不同的事物或者状态。这些事物或者状态,虽然彼此之间不同,却如家族成员般从属于同一家庭,而具备某些相似的特征。例如,在日常生活的语言里,“游戏”一词可指称各种活动,如下棋、打棒球、“人生是一场game”等。但这些活动却无相同的特质,只有家族相似性而已。正如一家之中,兄弟姐妹,个个长得相似,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不从属在同一个家庭。
以下是我们可以找到在一系列当今社常见的游戏活动,它们都以“Game”为共有名称,以“Play”统一命名在此类活动中的行为。
那么电子游戏又有哪些特征与传统游戏相似呢?我们再来进行类型列举分析:
以上多类游戏活动中play所指代的具体行为命名,我们会发现,确实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游戏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家族相似,所以只能用play来笼统地进行命名。但是这些游戏之间又并非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但游戏形式和具体游戏的规则是瞬息万变的,维特根斯坦时代所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游戏定义问题其实并没有今天这样复杂——新媒体崛起之后,大量的传统游戏活动被以编码的形式重新模拟编写称为具体的游戏软件,这才是游戏和玩家更需要被重新认识的原因。
虽然“家族相似”的提出,将游戏的“本体论”问题引向了一个通过认识游戏并为其命名的语言学问题,避免了方法论争执的必要,但这些看似共同特征和所谓内在规律,其实是人类因为自身描述的需要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这种从特殊现象到一般符号的思维方式是所有语言游戏的基础。
所以,当我们建立对游戏和玩家命名的分析时,需要回到具体的游戏活动想象中去进行把握。
我们将“Play”这一词汇的能指所对应的“游戏活动”进行映射,我们可以看到它作为一个动词,它标记的是一种人类活动。那么至少从这个角度讲,“play”是具有本质的,它的本质就是一种“人类活动”。
如Roger Caillois在其著作“Man, play, and games”所言:
“总结游戏的形式特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自觉地站在‘平凡’生活之外的‘不严肃’的自由活动,同时又强烈而彻底地吸引着玩家。”
到这里,通过本节内容中所讨论的传统游戏活动与电子游戏活动进行家族相似对比,我们会发现,电子游戏其实远比传统的游戏活动中所出现的形式都复杂很多。它对社会,对审美,甚至对意识形态都产生了不同侧面的影响。
那么要讨论游戏的社会意义,必然要先从游戏活动中玩家的行为模式去分析。
02
乐趣是游戏的核心要素

游戏不是人类独有的现象。我们通过观察小动物发现,动物天生就会玩游戏,不需要任何教育。并且人类游戏的一切基本要素,都体现在小猫小狗欢快的嬉闹中了——尽管人类的游戏规则更复杂、形式更先进,但从形式创新上说,人类并未给“游戏”这一概念赋予任何人类独有特征。
游戏似乎是一种生物本能,但用“本能”或者“天生”解释这个问题未免流于粗浅。长久以来,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尝试给游戏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最有市场的理论是行为心理学家们在20世纪初所进行的尝试——“通过游戏对幼年生物智力或物理上的某些机理进行锻炼”,以适应未来严酷的生存环境。其他研究成果还包括“释放过剩精力、放松身心、补偿落空期待、生物发泄某种先天才能的冲动”等等 。
赫伊津哈认为,以上说法都在逻辑上犯了同一个错误,即先入为主地断定游戏必定在为某种不是游戏的东西服务,具有生物学或功利的目的。这些理论完全忽视了游戏的“乐趣”,而乐趣恰恰才是游戏活动的核心要素。
游戏活动通过追求自由而获得的愉悦与乐趣,会导致以上结论苍白无力——如果具有目的的所有生命活动都可以通过机械锻炼实现,为什么自然选择和进化赋予我们游戏的能力?难道游戏只是一个没有具体所指的符号么?事实上,游戏行为远超出了人类生活的领域,也就不以任何约定或者被规训的理性关系为基础,如若不然,游戏现象便该限于人类专有了。
当代电子游戏的研究者和学者,穷究心智与时间,力图向世人证明游戏或者电子游戏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行业——但却被精通古代历史文献的先贤呵斥:“游戏并不追求有用,而是追自由!”
值得庆幸的是,赫伊津哈除了棒喝,还递给我们启发的火种:人的价值观不应该只围绕“有用”这一个维度来讨论。我们在物质之上构筑精神世界,而对游戏的思考也应该延展到那个领域:
“承认了游戏的存在,也就承认了精神的存在,因为不论游戏是什么,它都不会是物质。即便在动物界,游戏也挣脱了物质的束缚。如果认为世界完全受盲目力量支配的话,游戏就纯属多余了——
只有精神的洪流冲垮了为所欲为的宇宙决定论,游戏才有可能存在……人类社会超越逻辑推理的天性才能不断被证实。动物会玩游戏,因此它们不只是单纯的机械物体;我们会玩游戏,而且知道自己在玩游戏,因此我们必定不只是单纯的理性生物,因为游戏是无理性的。”
结合和赫伊津哈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游戏(game)是指人类的特殊活动,我们统称它为“play”。游戏活动是一类没有具体概念可以直接把握的人类活动,这些活动遵循着某种规则,规则之间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
根据以上的分析,“play”作为某种具有家族特征的行为活动,不但提供了特征,而且提供了“本质”,特征和本质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游戏家族的“特质”。具体说来,游戏特质就是这个集合中所有家族成员特征所依赖的内在结构的特性。游戏构成一个家族,其成员不仅是相似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共同的内在结构,即游戏的内在机制(比如说,要由一个或多个人进行操作活动)。
这种机制在游戏存在的每一个可能形式中是同样的,并且现实世界的传统游戏与数码世界的电子游戏,如果它们有相同的机制,那么它们就是同样的游戏。家族相似的分析法背后对游戏的内部结构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家族遗传密码”的结构。不管怎么说,一个家族总有它的遗传密码结构,并且如果在现象世界中的家族与编码世界或者语言世界中的家族有相同的遗传密码结构,那么它们就是同一个家族。
赫伊津哈论证,艺术是从游戏中诞生,并作为游戏发展起来的。然而游戏本身要发展成艺术,要面对其他艺术门类都没有的逻辑悖论:它还是游戏吗?各种艺术门类一旦发展成熟,即便它们在机制上还保有游戏元素,但也不再是游戏了——好比戏剧,在原始阶段就是游戏,待其发展成熟,被定性为“艺术”后便脱离了“游戏”范畴,但它仍是戏剧——保留了自己作为戏剧被规定那个的本质属性。
电子游戏不一定必要被归为“第九艺术” ,但不可否认的是,电子游戏是人类广泛的游戏活动(play)中产生的游戏家族(Family of Games)中的一员。它和其他传统游戏有着亲缘关系,而部分艺术如戏剧,音乐包括诗歌等也同样产出自古代人类的游戏活动,亲缘没有是非只有远近。
如果把电子游戏放入艺术的范畴中讨论,那么它还需要接受艺术体制的规训,而这对于电子游戏是一种二次桎梏。因为电子游戏本来就是以追求自由而进行的游戏活动中被抛下变成具体规则的游戏产品,再从对它进行第二次规范着实相比其初衷早已背道而驰。
03
总结

通过细分游戏活动中玩家不同的行为,以及丰富的精神活动状态,我们会发现,传统媒介理论只通过媒介划分来讨论“电子游戏”和“电子游戏玩家”的方法会产生大量的概念混淆。
传统媒介理论对玩家和游戏的理解,无法有效识别“电子游戏玩家”与“电子游戏职业劳动者”,更重要的是无法与那些认同“电子游戏成瘾论”的人群开展有信息交换的正确对话,致使大量的数据统计研究以及对电子游戏的社会管理失效。
“玩游戏”或许是一种在反复训练同时还需要随时带入反思状态的人类活动。我们仔细研究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定义会发现,游戏的定义其实不只界定了“游戏”的性质,对人的“游戏状态”也是有要求的,大抵包括参与自由、非功利、能随时终止等等。对于所谓的沉迷者,无法区分“游戏”与“现实”,无法靠自己的意志选择适时地结束这种活动,这种状态其实是很不具有“游戏精神”的游戏行为。
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是想“玩游戏”,只是现代劳动-空闲的生活节奏中,人们经常只想无意义地度过一段时间。按赫伊津哈理论,当我们处于这种状态下,也不能定性为“游戏”,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别无选择”并非纯粹自由参与了游戏活动的,且带有通过“游戏”打发时间的功利性。同时,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当我们在这种状态下玩游戏,往往无法体会到多少乐趣。
电子游戏作为模拟传统游戏活动的数位编码软件,它本身具有媒介理论所描述的特征,但电子游戏玩家作为人类,他们所进行的游戏活动,需要从传统游戏活动的理论中去找描述方法。
当我们清楚分辨了“play”与“game”的不同所指,我们才能识别游戏活动的特质,并理解赫伊津哈站在传统游戏理论对20世纪后人类游戏行为的批判与反思——如何在规则的枷锁中追求自由的超越。![]()
--------------- 往期回顾 ---------------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更多关于电子游戏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