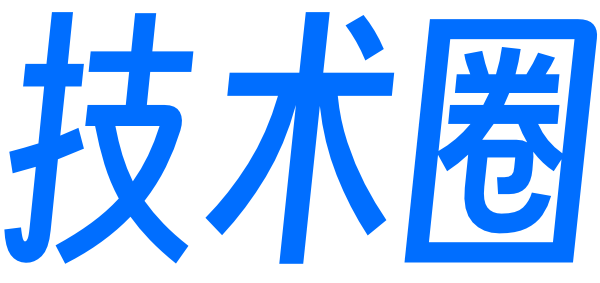底层程序员,出局

「在深圳,每个人都走得很快。」这是徐亮的体会。第一天搭地铁去IT培训学校,他发现前面的人突然开始疾走,接着小跑起来,所有人都开始跟着一起跑。他被挤在人群中,发现是列车的车门要关闭了。他也开始在站台上冲刺,刚好在启动前把自己塞进车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徐亮抬头一看,他其实坐上的是反方向的列车。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 人物
文|张炜铖
绿灯
电脑桌面中央是一个红绿灯,用编程语言让红灯、黄灯和绿灯依次亮起,一位合格的程序员能在两分钟内实现这一切。但11年前,19岁的孙玲第一次见到这个画面时还是被震慑了,她意识到,是技术让一切变得简单、迅速、直接。
那时孙玲刚得知自己高考落榜的消息,一个上升通道关闭后,她偶然接触到程序员这个职业,当即就想报IT培训学校,可是原本打算资助她的姑姑家里出了问题。后来,在手机电池厂的流水线待了一年后,孙玲攒了一些钱,决心脱离工厂,第一个想起的,还是红黄绿灯亮起的画面。
位于深圳华强北的一所IT培训学校让孙玲获得了成为程序员的入场券,她的传奇经历从此开始——通过自考获得文凭,不断跳槽去更好的公司,学英语去美国念研究生,最终在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直到今天,孙玲去过的这所学校依然在行业里活得很好,门口的沙发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沧桑的中年人,满怀信心的年轻人,焦头烂额的家长,都在这里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只要在前台填完一张信息表,各式各样的人——招生老师、培训老师、学校主管都会找上门来,热情地邀请你走上通往程序员的道路。
对于要来IT培训学校的人,孙玲是一个「神话」,在采访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提起她,怀着向往的神情。她是一个坐标,代表着一种可以模仿的跃升轨迹,就像去年刷屏的那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她用了10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这激起人的一种想象:一个毫无基础的普通人一旦成为程序员,就有机会在互联网的浪潮里开始一段不同于以往的、完全崭新的人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迫切地想找到通往互联网世界的入口,上一个IT培训学校,可能是花费最少、门槛最低的方式。
25岁的徐亮是其中一个。他选择的这家IT培训学校在深圳开了十年,规模保持在中等,一幢老旧写字楼里,塞进了四间教室和零散的小办公室。招生老师接待了徐亮,承诺他未来的工作「保底6K」,她在徐亮眼前比划着,「多的话拿到8K完全有可能。」她把招生宣传册推到他眼前,第一页印着:「选择IT,选择成功。」
徐亮将信将疑,环顾着培训学校四周的墙壁,贴的都是「就业明星」们的信息,他们的起薪没有低于10K的。招生老师继续给他勾画出明亮的未来:找工作、落户、做一个新深圳人——他被鼓舞了。
做一个新深圳人,一直只存在于徐亮的想象中。他在农村出生,小学上到一半,父母盘下一家小五金店,家里搬进只有两条主干道的县城。同辈的哥哥姐姐不是外出在工厂打工,就是留在县城谋生,只有一个哥哥是大家公认的「有出息」,在深圳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
2018年夏天,徐亮接到哥哥的电话,邀请他来深圳学IT。他不懂什么是IT,22岁的他当时在一家雕刻厂工作,是整个厂子里最年轻的雕工,老师傅们支使他买烟和槟榔,他从来不敢说不。有一天,他偶然和他们说起,自己可能会去大城市,学IT。「别说胡话了。」和他最亲近的师傅说,「你的脑子我还不清楚?不可能的事。」
徐亮撇了撇嘴,想反驳又无从说起,他在厂房门口回头看,雕刻厂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到处落满花岗岩的灰屑。一边是师傅们趴在石料上无休止地劳作,一边是新安装的数控雕刻机发出尖刻的响声,他觉得如果继续待下去,人生好像就栽倒在花岗岩上了。哥哥的电话再次打来时,徐亮决定动身,前往深圳。

快捷键
「我没有基础。」在IT培训学校,徐亮忐忑地问,「真的可以学吗?」
「只要你知道电脑的开关机,就可以学。」招生老师这么保证。
他去试听,从老师的操作中头一次知道了可以用Ctrl+C和Ctrl+V的快捷键来复制粘贴,他从中看出了「专业程序员」的味道,「程序员就是有一些独特的习惯,比如说会用很多的快捷键。」
厌恶学校生活的徐亮在培训学校找到了不同的感觉。上午四个小时课,下午和晚上是自习,到晚上十点,屁股都坐痛了,徐亮也舍不得走。学校的电脑很老旧,教室里常常传出学生们因为电脑死机骂脏话的声音,但徐亮总是很耐心地等。他需要时间停下来思考,才能跟上课程和作业的速度。
最开始教JAVA基础课,集合、多线程、数组、IO流,这些概念把他绕晕了,他刚把HTML搞懂,CSS3又来了。好在他学会了在网上检索教程,网上都有答案,这是他第一次运用叫自学的学习方式。
教材一共有六本,每本将近一百页,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填鸭式」,只教课本上的东西,没有进一步的扩展。学不懂的时候很多,不耐烦了,徐亮会到培训学校专门给学员设置的吸烟室抽烟,烟雾缭绕中,墙上「就业明星」的笑容依旧显眼。
之前在雕刻厂,徐亮一根烟可以抽半天,在这里,他的耐心只够抽半根。抽完烟,还得折回去,把不懂的代码段落背下来。在培训学校,没人讲代码背后的原理,实在学不懂的,要用的时候能默写出来就行。培训学校曹老师理解的是,他们奉行的是「应试教育」,不过「试」指的是企业的面试。讲到重点,他的习惯是拍一拍黑板,警告学生,「这是面试要问的。」
培训学校还安排了优秀毕业生回来交流,是一位在创业公司工作的JAVA工程师,工作一年多,他拿到了15K的月薪。徐亮看到真人,觉得从谈吐上来说,这人还不如自己。他的信心更坚定了,觉得自己很快会成为熟练按下快捷键的人。
「在深圳,每个人都走得很快。」这是徐亮的体会。第一天搭地铁去学校,他发现前面的人突然开始疾走,接着小跑起来,所有人都开始跟着一起跑。他被挤在人群中,发现是列车的车门要关闭了。他也开始在站台上冲刺,刚好在启动前把自己塞进车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徐亮抬头一看,他其实坐上的是反方向的列车。

速度一直是深圳的代名词,软件公司在这里的发展也是如此迅猛。1995年,IBM进驻深圳,随后,康柏、希捷、三洋、施乐等跨国公司纷纷在深圳开设分公司,带来了技术、岗位和钱,深圳变成了软件业的乐土,从2000年到孙玲入场的2010年,深圳软件业的企业数量几乎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
那时智能手机没有普及,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没有到来,市场需要的,是能写门户网站代码的人,JAVA已经是开发网站最常用的语言,但大学里还在教C语言——解决这个矛盾的IT培训学校应运而生。华强北、南山科技园、龙岗中心城,在互联网公司的边上,IT培训学校挤进写字楼里,用人公司会直接来培训学校开招聘会,每个公司占据一个小隔间,学生们排着队进去面试,不通过的人很少。
徐亮渴望能赶上深圳速度,在他的想象中,培训学校是一所魔法学校,教的是市面上最稀缺的东西,进去了就意味着好工作、好未来。而深圳的IT培训学校的教课进度,又是全国分校里最快的,从各个省份来的学员都急切地等待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别的分校教一年半的内容,在这里8个月能全部上完。课程除了JAVA语言,还穿插着开发网络电视精灵、新闻发布系统、租房网等项目,宣称把学员都培养成够格的软件工程师。它就像出现在人生里的快捷键一样,以最迅捷的速度把人生送到下一阶段。
人涌进来,培训学校也在疯狂扩张,2010年到2012年,最著名的北大青鸟IT培训学校在深圳开了6家分校。「学IT,好工作,就来北大青鸟」的广告词像咒语一样,铺天盖地出现在传单上和电视广告里。国内当时规模最大的IT培训机构达内教育,也在2014年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转变发生在2015年左右,风口期过去,巨头公司开始出现,庞大的系统对于代码的要求已经不是「能用就行」,而是要求简洁、漂亮、可持续优化。「企业都在挖掘自己的护城河。」十年前就上过培训学校的祝容说。这个护城河的核心是最优质的程序设计,它带来学历、经验、出身构成的壁垒。
护城河修好,普通人就进不去了,曹老师也清晰地感受到。他所在的学校,培训材料一年半更新一次,已经是行业内最快,而在那些大企业,「是真正的日新月异,一个月不学习,就会被公司淘汰。」培训学校也在逐渐被淘汰。2017年到2020年三年间,北大青鸟深圳分校从6家缩减到2家,小的培训机构纷纷关门,只留下过去处在头部和中部的机构。截止2019年底,达内教育的市值缩水了91%,并且由于拖欠财报,收到了纳斯达克的退市警告。
IT培训班的学员们接触到的课程——JAVA面向对象编程逻辑、JAVA高级实用开发技术和Web前端开发技术等等,从名字上来说,看似可以满足一个程序员的生产需求,但也仅仅是名字而已,培训班教的都是基础中的基础,知识过时而简陋。「同样是盖楼,头部互联网公司要求员工盖一座摩天大厦,培训班只能教你如何盖一间砖房。」一位资深程序员说。

进货
但圈层以外的一部分人对这一切毫无知觉,依旧想搭上这趟便车。几年前,22岁的曾峰从一所普通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苦恼于没有学到可以直接应用的技能,被广告吸引到IT培训学校。他对于学到什么已经记忆模糊,但他记得在下课后在厕所前排队的焦灼,人太多了,每次前面都要排六七个人才能轮到自己。
那时他了解到,IT培训学校还有一种班叫业余班,班里的学生大多来自流水线工厂或服务业,工作日需要上班,只有晚上和周末才能来学习。一般一个班只有一半的学员能学完所有课程,对他们来说,昂贵的学费、大量的时间,都是学习的阻碍。
但是无论是业余班还是脱产班的学生,在培训学校的招生老师蒋洁眼里都没有区别,他们要缴纳的学费是一样的,这意味着她拿到的提成也是一样的,每有一个人报名,她会收入2000块。
在培训学校,蒋洁没有基本工资,每一个潜在的学生都是她可能拿到的钱。她三年前入行时,IT培训行业已经没有那么景气,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越来越少,只有靠她主动出击。
每一个进入培训学校的学生,学校都要求他们再留下5个身边同学的联系方式,蒋洁会一个一个打过去,问有没有来学IT的意愿,如果没有,「那认识的人里有没有想学的呢?」如果有学员成功介绍新的学员进来,学员本人会得到一千块的奖金和两千块的学费减免。
另一种招新的方式,是从差一些的大学接手他们的学生。这些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会在大三暑假的时候开展「实训」课程,学校没有安排师资,就请培训学校的老师过来,作为交换,培训学校也因此获得了招生宣传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忘掉过去。」蒋老师传授招生的技巧。「无论对方过去是什么样的,先表示同情,再告诉他们,不重要,然后展望未来。」她最擅长于对付忧心忡忡的家长,他们往往为了孩子的出路发愁,这时候她会说起自己不存在的「哥哥」和「弟弟」。
「我的弟弟也是,沉迷玩游戏,玩得那个性格都变得很古怪。」
「我哥哥之前没有读书了,想出来打工,玩了两年也没有正经工作。」
「我就叫他来学这个编程,现在已经上班了。」
「挣得不算多,但是可以自食其力。」
学费不便宜,在2万上下,各个培训机构都是这个价。但交不起学费也没有关系,可以使用互联网金融APP的学费贷款功能分期付。招满了15个人左右就开班,中间陆续再添进来,最后的规模在30人左右,而这30人里头,大概有一半为了交学费而申请了贷款。
蒋老师经常在朋友圈晒一类微信聊天截图:又有HR找上门来,邀请培训学校组织学生去公司面试,岗位丰富,包括软件开发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等。她还会配上文字:「就业合作企业HR再次发来人才需求橄榄枝,享受一流企业福利和待遇。」
聊天截图的另一头,是互联网人力外包公司的HR赵丽。「HR」是她的自称,实际上,行业里的人都管这一类岗位叫做「销售」。她的工作就是向甲方用人单位贩卖人头。她介绍从IT培训学校毕业的学生去甲方面试,面试通过后,学生为甲方工作,拿低廉的工资,合同签在人力外包公司这里,甲方再付给人力外包公司一定的费用。
招聘的要求越来越高,培训学校的产出跟不上市场的需求,简历造假开始出现。但赵丽从来不介意这些学员的简历是真是假,她在意的是自己的指标和提成。一个月里,她会介绍150个以上的人去甲方面试,如果有人能通过甲方的面试留下来,成为正式的外包员工,她可以从公司那里拿到1000元的提成。「除了人力外包公司,没有人会主动去找培训学校。」她说。「我去培训学校,就像是从批发市场进货,货的质量我不管,卖得出去就行。」而假的简历,意味着可以「卖」得更容易。

全都是假的
徐亮终于到了要正式面试的时刻。
培训学校先是举办了一个分享会,让每一个人上去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说自己的过去,他因此知道了同学们的来历,售楼员、餐馆的服务生、被金融业淘汰的人,也有学业不精的大学生。在接连不断的抒情和反思里,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有一个同学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他大专辍学,但在培训学校里,他是学习委员,每天负责给同学们开电脑。徐亮感受到了胸腔中的共鸣,他们确实是一样的,他想,都是之前不够努力,然后现在要拼一把的人。
有的同学之前做文员、工人,一个月拿三四千,现在不过培训了四五个月,出去就能拿翻倍的工资?学员自己也不相信,在面试的时候不敢提这么高的薪资,培训学校的老师给他们上思想课。「你们是时代需要的人才。」「就应该拿这么高的工资。」「不要露怯!」「大胆地提!」
互联网企业的程序员招聘流程一般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看简历,二是技术面试。在技术面试上,面试官会就一些基本的编程语言与框架向求职者提问,考察技术水平。因为没有实操环节,所以只要口头上能够答出来,就能顺利通过。至于简历,培训学校有别的办法,技术课上完了,该上职业素养课,老师走进来,先跟他们讲:「简历需要包装,所有人都包装,你不包装就是落后于别人。」
徐亮点点头,有些同意这句话。老师接着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年龄,写上1-5年的工作经验。他没找过工作,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旁边的同学小声嘀咕,这不就是造假吗?于是徐亮问他,「造假的事情,我们能做吗?」
同学没回答他,他自己也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想起周末的时候和同学去深圳后海一带玩,那里有腾讯大楼和数不清的互联网企业,写字楼的外墙在海边的太阳下发光。他发誓要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坐在空调房里,让别人都来服务他。
徐亮还是照着老师的话做了。他1995年出生,老师让他写上三年工作经验。公司名称,叫他去网上找一个听起来像样的小公司的名字;项目经验,就写在培训学校做过的项目,如果嫌培训学校里做的不够高级,就再去网上找,徐亮在网上找到一个清华大学的软件项目,听了一半,把这个项目的名字写上去了;学历,用在培训学校「全自动」获得的成人高考本科,这一类本科文凭只要交钱,不需要上课就可以包过,毕业年限随着设定的工作年数可以随意变更。
「你要是不能接受,就编少一点。」老师也这么劝过曾锋,要求他修改简历。他拒绝了老师的要求。老师不允许。他问,我不找工作行了吗?我直接回家。但入学的时候签了协议,学校要负责学生找工作的一切事宜,不能轻易地放他回去。他就办了休学,名义上是中断学业,和老师说他明年再来,回了老家。
有全日制本科计算机专业毕业证的谢飞,在经过培训学校的简历「包装」后,开始了求职之路。他算了下,自己至少投了500份简历,最开始的时候,只去离自己10公里之内的公司面试,后来这个范围扩大到15公里、20公里,到最后变成了整个深圳市都可以。
有面试官委婉地提醒:「你的简历和经历不太匹配。」他答不上话来,明白简历被识破,汗落了下来,分不清屋子里是热是冷,只想快点逃离。但是很快他就克服了这种情绪,因为面试的场数太多,他对一切都已经麻木。最终一家销售公司要了他,在这个公司,只有两个技术岗,所用到的代码可能在5年前就已经被大公司淘汰。
即使找到了工作,假的简历对一些人来说依旧是炸弹一样的存在。陈龙本科学的是光电信息科学,这个专业能找什么工作,他完全没有头绪。于是他在2017年报名了IT培训学校,后来转行。工作的两年里,他总是极力回避去当新人的面试官,看到别人的简历,他就会想到自己那份——不仅学历、经验是假的,连年龄也是假的。当同龄的同事谈论起年龄有关的话题,他只能保持沉默。有一次别人问他工作时最看重什么。他说,是诚信,心里想的还是那份假简历。
洗白简历的方法一般是在工作一两年后,等有了真正的工作经验,就跳槽去新的公司。但是陈龙重感情,希望能和现在的同事们继续共事。在他入职一年多时,他找到了一个和直属领导吃饭的机会,在饭桌上向他坦白了。
「我知道,我其实看出来了。」领导听到之后一点吃惊的表情也没有,非常淡然地说。他更加无地自容了,想到自己在过去的工作中一定出现了很多疏漏,才会让人看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领导没有再提这件事情,就剩他一个人继续煎熬。结束了一个大项目,同事们一起去聚餐喝酒,他依旧是心事重重。在嘈杂的交谈和玩笑声里,他一声不吭地喝着,不自觉喝到神智都有些模糊。「我的简历是假的!」他突然大喊出声。同事愣住了,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走到他身边,问他,「怎么了?」「假的!全都是假的!」他跪倒在同事面前,继续道歉:「我的简历是假的。」所有人都听见了。后来他才从一位关系好的同事那里得知自己做了什么。公司的氛围依旧保持着平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从此,他再也不在公司聚餐上喝酒。

外包
来不及去仔细研究每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只要标注了「软件工程师」、「JAVA工程师」等字样的职位,徐亮都投出了简历。最终他被一家小公司聘用,月薪是6-7K。签完入职协议,他回过头看公司介绍,主要合作对象写了一大堆,从政府机构到影视公司,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家项目外包公司。
项目外包公司是乙方,负责从甲方承包项目,是依据甲方的需求进行软件开发。没有自己的产品,工作内容和进度全依甲方而定。如果在网上询问要不要去软件外包公司就职,得到的几乎都是千万别去的忠告。但徐亮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报班的时候贷了款,学费是两万三千多,还没开始找工作,催还款的短信就已经发到了手机上,必须要找到工作,这念头在他脑中绷成了一支弦,催着他干一切事情。
他终于来到了深圳软件园,第一天上班坐地铁,已经习惯深圳节奏的他顺着人流从地铁走出来。「真得劲。」他脑子里满是雀跃的想法,差点在地铁口的台阶上摔一跤。但等到真正开始工作,他心里的一丝侥幸马上就消失了——因为自己实在太「菜」了。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不敢问同事问题,怕显得水平太差。后来每完成一段工作,就强化一次这样的想法。有一次主管给的deadline太紧,他不得已在淘宝上找了程序代写,但是代写的人水平也不高,他俩一起研究方法,才按时提交任务。
在培训学校的分享会上,徐亮说出自己高中辍学的原因:他上课看网络小说被班主任发现,班主任强迫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出刚刚看的内容。他本来就成绩差,当下更觉得受了羞辱,从此也总是疑心老师和同学看不起他。现在,那种羞辱感又来了,开会的时候,主管问他:「程序日志怎么写的?刚上大学的小孩都不会写成这样。」徐亮察觉到有几个同事也跟着赞同地点了点头。他觉得委屈,他又没有上过大学,他怎么知道。
但后来他没那么容易退缩了,哪里被说不好,他就改正哪里。同事里技术水平最好的是一位工作了一年的计算机专业科班生,他专门去请教他关于框架的问题,技术论坛也看了不少。
距离他第一个项目的交付日期只有几天,他几乎是住在公司。他住在坪洲,离软件园只有20分钟,但是他舍不得花上这么一点时间。他开始计划,等这个项目做完了,要尽量多接触一些不同的项目多学习,在这里肯定待不到一年,之后可以跳去别的公司。
离交付日期还有两天,他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半,在公司楼下等车回家,主管的电话突然打过来,他接起来,然后就听到了噩耗:「甲方改需求了。」他当下就懵了,一整夜没睡着。
谢飞也是如此,他所在的销售公司业务很简单,但是对刚从培训学校出来的他来说却不好对付。谢飞总是偷偷地上网查某段代码要怎么敲,公司里唯一的程序员同事坐在他身边,时不时凑过来问问他进度如何,他赶紧把网页叉掉,生怕对方看到。等他适应了这家公司的节奏,他又很快意识到,这样工作下去没有任何进步可言。他重新找工作,在没有什么选择的情况下,进了一家人力外包公司。
在培训学校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说,有毕业学长带回来了工作机会,让大家都去看看。去了他才发现,所谓的工作是去柬埔寨开发赌博软件。他想,人力外包公司至少比非法博彩业好。谢飞甚至不知道他签的这家公司地址在哪里。他在甲方提供的驻场工作,合同中不属于甲方,位置上不属于乙方。没有谁能给他提供归属感。
等待着谢飞的是习以为常的加班和无穷无尽的项目,他也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东西是如何发布、如何被使用的。外包员工加班不用给钱,老板常常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发布任务,等到做完,就只能赶地铁的末班车。
「就像对着空气敲代码」,他这样形容。「你只是一个人力资源,和桌子、椅子一样,都是可以被随意替代的。」

徒劳
一家外卖平台曾经拍过一个宣传片,说的是一个程序员给一家互联网公司送餐,看到代码出了问题,像天降救星一样坐下来帮他们排除bug。「送外卖只是为了活动筋骨。」宣传片里的程序员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不如去送外卖——这是徐亮和同事们常开的一个玩笑。入职两三个月,最初的激情退去,在加完班的夜晚,他疲惫地躺在床上,经常自嘲式地想起这个玩笑:送外卖是搬运食物,自己是搬运代码,都不产出新的东西。
有时候他心血来潮,想优化一下程序,但是又觉得没必要,他不会因为创造出质量更好的程序受到额外的嘉奖。他工作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完成任务,任务多到他喘不过气,他最好的解压方式是,幻想自己要如何帅气地辞职,要怎么去气他看不顺眼的主管。工作半年,他身边同事已经换了一拨,那位技术好的大学生也离职了。
大概是今年5月,徐亮的右手腕开始痛,敲代码的时候手都很难抬起来,应该是腱鞘炎,同事笃定地给他诊断了。徐亮不愿意去医院,自己才工作不到一年,就说得了腱鞘炎,矫情。
那天,深圳大雨,一个项目在几天前收尾,新的项目还没来,公司里每一个人都神情怠惰,徐亮回顾了工作的10个月。「我每天都写这种脏东西,一天比一天脏。」类似的想法在他心里盘桓。「脏」,是程序员用来形容冗余过多的代码的词。他看了看周围,突然就无法忍受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过去设想过的辞职的场景出现在眼前。他走去主管的办公室, 「老板,我想和你聊聊辞职的事情。」「好啊。」主管静静地听他说完,没有说任何一句挽留的话,很快地交待了他手续要如何办,还送他出了办公室的门。
徐亮走出公司大楼,雨下得更大了。一切又回到原点,他想。外包公司的工作经历并不是什么好的加分项,在这个行业,外包公司等同于技术含量不高,现在找工作,他极大可能还是进另一家外包公司。他跑了三四场面试,放弃了。
他培训学校的同学和他有联系的不多,最亲密的一位最初去了一家创业公司,后来被辞退,再一次进入找工作的漩涡。他隐约听说,班上唯一的女同学,已经回老家嫁人了。「大部分学生都是这样,干上一两年,就回到原本的行业里去了。」曹老师说。
曹老师教过业余班,他有一位姓赵的学生,在数控厂工作,为了求得每天晚上都能上课的机会,找关系让主管把原本三班倒的工作时间都排在了白天。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是班上最好学的那一个,也很有天赋。但是曹老师依旧看见他的神采一点点熄灭下去。这样的生活不是谁都能坚持的。赵同学在课堂上逐渐撑不住了,开始打瞌睡。起初曹老师还会把他叫醒,之后却舍不得打扰他,强撑了半年多,他渐渐跟不上班上的节奏,也退学了。
徐亮也觉得迷茫,他终于明白「神话」孙玲只是极少的孤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培训学校、做一个底层的程序员,更多只是徒劳的一跃。要不要去送外卖?他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情,唯一的担忧是,他的右手腕即使不再敲击键盘,也会产生持续的疼痛。

一位兼职送外卖的程序员在路边打开电脑调整代码 图源视觉中国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孙玲外皆为化名。)
-END- “养码场” 现有技术人80000+ 覆盖JAVA/PHP/IOS/测试等领域 80%级别在P6及以上,含P9技术大咖30人 技术总监和CTO 5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