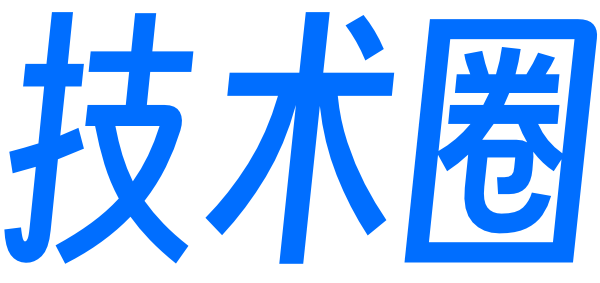在算法演进的历史中,为什么说游戏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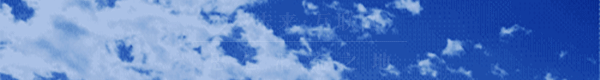

“随着早期计算史研究的不断推进,游戏在世界各地数字革新中的作用,亦日益凸显。通过游戏,许多早期开发者理解了计算机这个物理意义上的黑箱,跑通了人生中第一个算法。”
文 | 朱悦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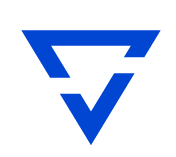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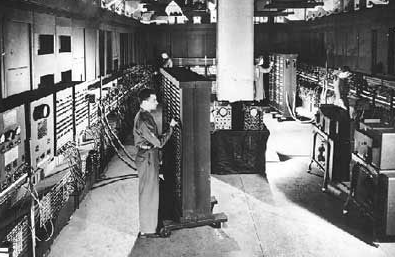
……你只要开机,基本上你就得编程。实际上,你也只能干这个。那时候,如果你不会编程,电脑就没啥用。你只能干些很蠢的、很初级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买游戏、玩游戏,但最有范的事,还是你自己写一个游戏。如果你不这么做,电脑就没啥用。

达特茅斯,成了个为计算机而狂热的学校……
学生在项目上完成的最有趣、最复杂的项目里,有许多是游戏……
秉持前述精神的游戏,应当成为今日编程教育的核心之一。唯此,用户方可在黑箱面前,保守已然失落的主体性。

对那些未尝接触数字交互媒体的人们来说,对早期的电脑游戏,他们怀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怀旧……
有一天,爸爸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们说,‘孩子们,你们可得过来一趟’。我们马上开车过去,那里有一台ZX Specturm……我们玩了附带的五个游戏……彩色的,会动,太不真实了。我们在那里待到半夜……这一印象太过深刻,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个人计算机总是声称,它们能做到一切,实际上,它们什么也做不到。有了红白机,我们首先承认,我们的计算机什么也做不到,除了能玩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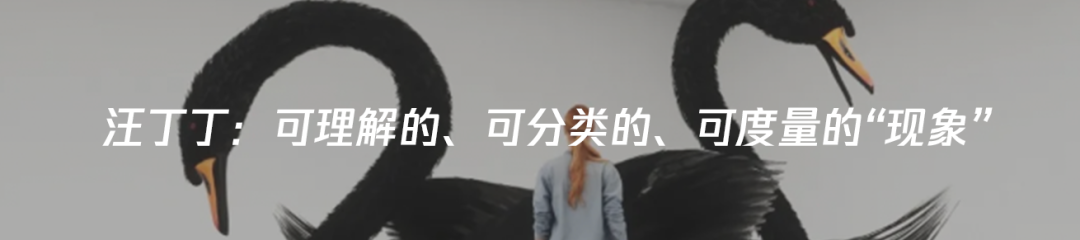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