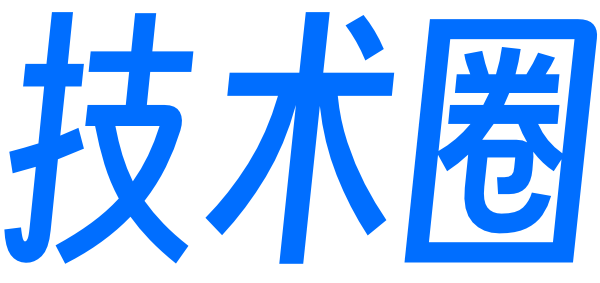纹着Maradona的男人和他们的喀什足球岁月
1
午觉醒来拿起手机,看到三个未接来电,都来自张哥。要说的内容,他在一条未读微信里做了说明:“晚上7点半有喀市足球俱乐部练球。”
欧洲杯后遗症和最近几天的正常时间工作让我有点儿乱,更何况在喀什,日落要到22点08分,到底该几点睡几点起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反正每天都犯困。
我把电话拨回去,他说:“反正来了,你应该去看看这儿踢球的孩子,我在路上了,离你还有3公里。”容不下我拒绝的口吻。
那是18:30左右,我去洗了把脸,来不及剃头,张哥的车已经到楼下了。
张哥是三年前我背包走到喀什时遇到的,他开车带着我和路遇的朋友们一起,意外穿行了塔莎古道。当时那条线路知道的人不多,路况极为糟糕。途中一个朋友打不开车门了,张哥停车下车,发现是脚踏板一侧断了,卡住了车门。他上下使劲,折断了整个脚踏板,扔在路边,潇洒地说:“门能开了。”
有朝一日,我得专门写篇张哥的故事。但眼下,如果没有他的贴身式热情,我也没机会去到喀什的夏马勒巴格镇,遇到那个在左臂内侧纹着“Maradona”的男人了。
2
在喀什,所有的计划都是没有计划。好比我坐上了张哥的车,接上了他的爱人和女儿,时间已不富裕,本该直接去看训练的,他却顺势停在了“馕产业园”,非要“用5分钟带我看看,顺便买几个馕”。计划顺利,但用了大概13分钟。
他不会预先告知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我只能在地图上搜索自己的位置。夏马勒巴格镇周边,进镇子的入口不太好找,我们顺着“←迪斯倪乐园”的招牌一路前行,在“迪斯倪乐园”旁边找到了球场。我佩服创作者的谐音能力,乐园里的一切设施,丝毫没有正牌的豪华,简单得像我们的童年,有种快乐没规矩的感觉。
进入正题。一个看起来没完全睡醒的朋友走过来和我们握手,并带我们走进了镇子一角的球场。人造草皮,我踏上去,不软也不硬,不好也不坏,用了许多年的样子。

我不知道张哥跟他介绍了多少关于我的内容,也不好意思打听。当然,从他的反应我能判断,他根本不认识我。
眼前是一群踢球的孩子,大约40人,都在6岁左右。而接下来的对话,如果按照现场的节奏,那就尴尬的要命了。睡不醒的哥们儿的口音很重,回答很慢。我努力从他的话中寻找关键词进行追问,但再回答的内容,大多也听不明白。
节约时间叙述一下我获得的信息:
这家名为丝绸之路的俱乐部,早在2002年就建立了,但到了2008年,由于地方足协支持度以及教练资源等原因,停摆了7、8年。
睡不醒的哥们儿叫麦吾兰,是俱乐部负责人。他曾经在四川冠城俱乐部梯队踢球,在冠城解散之后,去了秦皇岛。我问他当时在那家俱乐部效力,他似乎说了,我听不懂。
后来,他因为妈妈身体不好,返回了喀什,从父亲手里,接过了这家停摆许久的俱乐部,并重新运营起来。

眼下这些孩子6、7岁,也有5岁跟着一起练的,这是他们在正规指导下踢球的第15天。每个月的训练费是380块,俱乐部提供一套球衣,每周6练,每次训练1小时到1个半小时。
我算了算,折合每天,训练费大约是15块。
“孩子有的是,教练不够。”麦吾兰慢悠悠地说。
3
麦吾兰给我引荐了一位中年大汉。这回更尴尬了,不仅我们双方不知道对方是谁,甚至连对方要做什么都不知道。
大汉告诉我:“这些娃娃今天是第20天训练。”
得,一下儿跟麦吾兰介绍的差了5天,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趁着他们训练,我拍了张照片,发给了从喀什走出去的国脚买提江。很快,他的回复来了:“我舅舅”。

大汉叫居来提·祖农,出生于1969年,1984年离开喀什,去乌鲁木齐运动学校就读。1987年返回喀什,修完喀什师范学院体育系之后,从1991年到2018年,一直在喀什市第九中学当体育老师,27年的时间里,一直负责学校的足球队教练工作。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我通过文字采访的内容,当时是不知道的。
2011年,居来提成为了喀什儿子娃娃队的教练。这支球队因为参加中央电视台《谁是球王》节目,而一时名声大噪。居来提拿手机翻出了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我甚至辨识不清楚他指的人是不是他自己,反正背景是北京的鸟巢。
居来提指着场地里的一位年轻教练说:“他就是当时队里的主力中后卫。”
当年的徒弟,成为了今天自己徒弟的师父,这句话着实拗口。但确实,是喀什足球一代代传承的基本状况。眼下这两个徒弟都留在了喀什,在当地的俱乐部踢球。
居来提还有很多的徒弟,都早早地离开了新疆,在内地站稳脚跟,比如效力于上海海港队的阿布拉汗·哈力克。
2012年9月,11岁的阿布拉汗从莎车县恰热克镇去到了喀什。当时,他并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甚至遭到了周围亲戚的反对。在喀什,阿布拉汗停留了一年。
“居来提教练其实只带了我三个月”,阿布拉汗说。“他人特别好,把我当做家人一样,教给了我好多事,还带我去他家一起吃饭。训练的时候他要求特别高,三个月里我的进步很大,我想谢谢他。”

2012年,喀什足球的环境远逊于今日。发给阿布拉汗的足球鞋,要穿一整年,发的衣服,要穿无法以时间单位计量的“很久很久”。“我们每天聊足球,聊我们喜欢的球星,聊我们这边的训练和比赛。”
离开喀什之后,阿布拉汗在2014年加盟了陕西老城根,2020年加盟了河南建业,2021年去到了上港,并成为了在中超联赛登场的球员。
居来提给了我一个短短的名单,是那些他曾经带过的球员,如今都出现在中超中甲的赛场上。
除了阿布拉汗之外,还有艾菲尔丁、伊利亚尔、米尔杰提、买买提热夏提、穆太力普、伊尔夏提、希尔扎提。
那些孩子都纷纷离开了喀什,进入了全国各地的职业俱乐部,但居来提一直留在了喀什,他清楚地记得每个带过的孩子的名字。
4
2004年,木热合买提江离开喀什,进入山东鲁能足球学校。当时,13岁的买提江一句汉语都不会说,行囊当中,必不可少的是馕。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到内地发展的新疆球员里,买提江是毫无疑问的先行者。

我们曾经在录节目时聊到过那段经历。当年中央电视台去喀什拍了条专题,主人公是买提江的姥爷,带着当地的孩子们踢球。因为那次节目,鲁能足校的工作人员觉得买提江这孩子不错,因此把他带到了山东。
买提江的姥爷和舅舅都已经在本文中登过场了,而他的父亲也曾经踢过球,但是没能踢进职业球队。“踢职业足球是我爸爸的一个梦想,但因为各种原因,被迫不得不放弃选择。”买提江说。
实现梦想的接力棒传到了买提江手中。他描述了离开喀什之前的日常场景:
“我们都是一周回一次家,每天早上5点起床,5点半到6点早操训练。回来吃早饭、打扫卫生,然后8点上课,一直到12点。下课午饭后有两个小时午休,下午3点训练,无论打雷下雨还是下雪。场地条件非常差,土场的场地,土很容易往上返,每天训练完额头都是泥土。赶上下雪,我们会用早上课间时间出去铲雪……”

喀什的冬天,温度会低过零下10摄氏度;喀什的夏天,最高温超过35摄氏度,还伴随着极强的日晒;这趟去喀什,我就是在阳光下“一天黑”的亲历者。
仔细想来,祖孙三代的努力加上中央电视台加上鲁能足校,买提江走向内地的机会,成因复杂,缺一不可。
祖孙三代,这话说得多简单啊。可得是每一年里的每一天,都像买提江的日常那样过啊……
5
训练课时间并不长,居来提把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给他们排上了座次。曾在儿子娃娃队踢过中卫的年轻教练走来邀请我,一起合个影吧。活该我手懒不剃头,这次留下影像证据了吧。

居来提很细致,他安排每一个球员,去到理想当中的合影位,保证大小个儿错落有致,每个人都能露脸。我在猜想,到底过往有多少像我这样不明身份的人,以了解新疆足球为名义的人,在这块场地里合过影。
在所有仪式感的内容结束之后,我终于好意思提出我的问题了。早在我刚到球场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居来提教练左臂的纹身。

图像比文字更好描述“Maradona”到底纹的多么歪歪扭扭。“哪年纹的?”我把问题抛了出去。
“1986年。”居来提挂着笑,看不出是开心还是羞涩。“但是,1982年我在乌鲁木齐的时候,看比赛就有这种感觉了,到1986年,才纹了这个。”
我也无法翻译“有这种感觉”是种什么感觉,但就是莫名其妙地懂了。大概就像居来提的身上纹身只次一处,如此的突兀,就像他看到马拉多纳踢球那样吧。
“你的偶像是谁?”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阿布拉汗。
“小时候的偶像是买提哥,我的奥特曼哥。”他回答。
阿布拉汗和买提江年龄差十岁。2011年,阿布拉汗十岁的时候,买提江已经是中超第2年了。
居来提和买提江接触足球都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居来提在人生路上看到了马拉多纳,引导着他在基层一线工作至今;买提江因为自己的足球家庭,获得去内地的机会;阿布拉汗为了踢球遇到了居来提——他偶像买提江的舅舅。
喀什的足球血脉盘根错节,每一次人和人的相遇,都是一段新故事的开篇。眼下这些刚刚开始踢球的孩子,大多凭的还是兴趣。但很快,他们就会找到自己未来的道路,和自己的那个引路人。

如今,阿布拉汗已经和买提江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他说:“我们的故事不多,但是他一直很关心我宽容我,每次训练都给我指导,比赛前都会找到我给我加油,感觉像是我有血缘关系的亲哥哥一样。”
如今,买提江每次回到喀什,都会去探望舅舅居来提,和他教的孩子们,买提江希望能给他们带去鼓励:“现在很多球队都有新疆球员,这是一件让我非常开心的事。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和媒体,都普遍认可了新疆球员。只是我希望,有更多新疆球员,能在更年轻的时候走出新疆。”
如今,居来提仍是名带孩子踢球的一线教练。暑假之后,居来提的教练履历,整整三十年。“足球是从小陪伴我的运动,也是我祖传的运动。我想把我脑海里最实用的足球知识传给下一代,想给咱们中国足球贡献一份力量。”

眼下的奥运会,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金牌选手的诞生。每四年一次,我们因为金牌,在意许多项目的甘与苦,但难以体验他们四年间的甘与苦,更难详尽地了解每个人背后的人与故事。
从买提江的姥爷,到阿布拉汗,远不止四年,而是几十年的喀什足球,也是几十年喀什足球人的日常生活
离开球场之前,我问了居来提一个很俗套的问题:“接下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居来提笑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停了几秒,努力吐出了五个字:
“唉,一辈子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