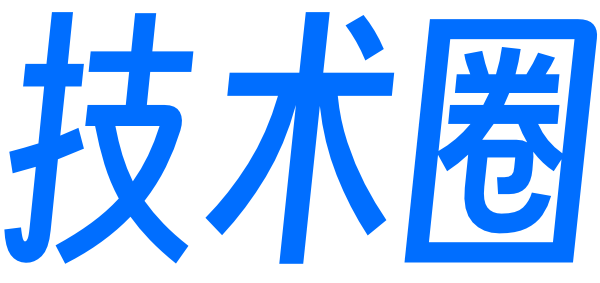一部宪法与一个国家

一.“打出来的”和“谈出来的”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些奇怪。她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在美国人的建国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与众不同的是,胜利后的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那些手握兵权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也没有趁机登上王位。也就是说,他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战争胜利四年后,即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被迫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部宪法。又过了两年,即1789年,宪法才被通过,联邦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人民也才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直到这时,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然而美国的建国日却定在十三年前,即1776年的7月4日。这是他们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这时,为期八年的“美国革命”才刚刚开始一年。那时的美国,既没有总统,也没有宪法,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政府,当然也没有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而只有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理想”。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建国了。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竞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
那么,在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国家机构这三个环节之中,哪一个最重要呢?应该是宪法。因为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理念,不是一个国家;而如果只有政府和总统,则美国未必是美国,没准还会是伊拉克。可以这么说,正是美国人在1787年起草的这部宪法,不但使《独立宣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而且保证了这个现实的国家最大限度地符合《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因为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背这些目标时,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惟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恪守了他们制定宪法时许下的诺言,并为确保《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不受伤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二百多年来,美国的宪法没有修改过一个字,而所有违宪的或者有违宪嫌疑的行为都受到了惩罚或付出了代价,当事人不是遭到国会弹劾,就是自动辞职下台(如尼克松)。就连华盛顿这样在我们看来当之无愧的“国父”,也是在宪法被批准之后,才由美国人民根据宪法选举为第一届总统的。所以我们说,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然而,这就把一般人心目中的建国程序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那里都是先建国后制宪的。但正是在这种“倒行逆施”中,人类追求了上千年的宪政精神才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种精神认为,不是国家创造了法律,而是法律创造了国家。美国的建国过程便体现了这一精神,美国也确实是最地道的宪政国家。惟其如此,美国宪法在1789年生效以后,世界各国便纷纷效尤,相继制宪,并以此作为自己立宪的参照系甚至楷模。
这也毫不奇怪。毕竟,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依据这部宪法选出的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选总统。根据这部宪法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则是最典型的共和国。它甚至被称作“共和国之祖国”(梁启超语)。而且,正是由于它有着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共和制度和宪政精神,这个国家在不过一二百年的时间内,迅速由一个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松松散散的联邦之国,崛起为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其影响之深远,已让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望尘莫及。可是,这部宪法在形成过程中,却差一点胎死腹中。
首先是制宪会议开得很不顺利。这次会议的时间原本定在1787年5月14日,正式代表七十四人。但结果,实到只有五十五人,而且拖到5月25日才达到法定人数,正式会议因此延期十一天。会议开始以后,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场的又有十三人,坚持到底的只有四十二人;而这四十二人中,又有三人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罗德岛则始终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样,最后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只有十二个邦的三十九名代表,包括他们的主席、弗吉尼亚代表乔治·华盛顿。再加上一个证人、会议秘书威廉·杰克逊,签字的一共四十人,只不过比七十四人的半数稍多一点(百分之五十五)。至于会议过程中充满唇枪舌剑和讨价还价,则更是不在话下。所以这次会议便从1787年的5月25日一直开到9月17日,足足开了三四个月之久。最后,许多人最初的意见,都被别的代表修改得面目全非。对于珍视自己思想的人而言,这种结局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华盛顿认为,这部宪法能维持二十年,就算不错了。
随后,好不容易才草成的宪法,在交由各邦批准时又遇到了麻烦。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三个邦倒是爽快,当年就予以通过:特拉华和新泽西的议会一致通过,宾夕法尼亚则以2:1的票数通过。到1788年6月,批准联邦宪法的邦已达到法定的九个,但还有两个举足轻重的邦,即弗吉尼亚和纽约,迟迟不肯批准。这样,又经过一番斗争和妥协,这两个邦才勉强同意批准,美国宪法也才得以于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一个“神形兼备”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但恰恰是这种特殊的国情,不但决定了这个国家是谈出来的,是由宪法和法律创造的,而且决定了它的宪法也一定是最能体现共和与宪政精神的。
二.从殖民地到合众国
多少读过一点美国史的人都知道,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北美大地上并没有什么国家,只有一些殖民地。它们在理论上属于大英帝国,实际上由自己管理,即“主权王有,治权民有”。在1607~1732年之间,这样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有十六个。后来,有三个殖民地被兼并。因此,到独立战争时,北美大地上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是十三个。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它们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所谓美利坚合众国,起先就是由这十三个殖民地联合而成的。
把它们联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这些殖民地虽然都号称英属,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瓜葛。每一个殖民地都是以个案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政治权力直接来自英国国王的特许。大英帝国对它们进行“垂直领导”,并没有在当地设立过统一管理这些殖民地的政府机构。所以,这些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关的,也是可以互不买账的。
其次,这些殖民地的性质也不相同。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就是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马萨诸塞,则是马萨诸塞湾公司建立的;第二类是领主殖民地,是英国国王封给某个或某些领主的。而且,就像当年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这类殖民地也可以再分封。比如以英国王后玛丽命名的马里兰,就是封给第一代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的,而巴尔的摩勋爵又分封了六十个庄园;第三类殖民地是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它们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领主,是自由移民自己根据他们之间的契约建立起来的,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就是。这三类殖民地,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并不那么容易就能拢起来。
第三,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也很复杂,有白人,也有黑人。白人当中,除英格兰人外,还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瑞典人等等。根据1790年的统计,当时的白人中,英格兰人占百分之六十点一,苏格兰人占百分之八点一,爱尔兰人占自分之三点六,德意志人占百分之八点六,荷兰人占百分之三点一,法国人占百分之二点三,西班牙人占百分之零点八,瑞典人占百分之零点七,其他人占百分之六点八。这说明北美殖民地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多元文化社会。多元必多样,也必定多心,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况他们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哪里就能一下子统一起来?
最早是在1754年的6月,有七个殖民地的代表在阿尔巴尼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只是为了应付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威胁,是一次临时的动议,但这些殖民地能够想到结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联合开始了。
十一年后,即1765年,又有了一次“反印花税法大会”。这次大会是根据马萨诸塞的倡议在纽约召开的,有九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克里斯托弗·加兹顿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的概念。他说,在这个大陆上,不应该再有人自称新英格兰人、新约克郡人,我们都是美利坚人。这个说法得到了人们的响应和认同。于是,生活在北美英属殖民地上的人民第一次有了共同的民族概念,美利坚民族诞生了。
又过了九年,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来自各殖民地的五十五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通过了《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向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一些“不可容忍的法令”,并同时决定一致抵制英货,停止对英出口。
这种原本有限的反抗却被英王乔治三世视为叛乱,他宣称这些殖民地人民“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英国)还是独立”。殖民地人民也不含糊。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独立战争打响了,而且一打就是八年。
实际上,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的那些北美英属殖民地,现在已变成了“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也有了合众国赖以孕育的母体。1776年1月5日,新罕布什尔率先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自己“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其他北美英属殖民地则在两年间纷纷效法(马萨诸塞则在1780年6月16日通过新宪法,以取代1776年的旧宪法)。这样,原来的“殖民地”(Colonies),就变成了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State),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宪法和依法成立的政府。惟其如此,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才可以这样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
不过,1776年7月2日,当大陆会议讨论是否公布《独立宣言》时,特拉华代表约翰·迪金森却投了反对票。九天以后,迪金森又向大会提交了一个法案,即《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这是《独立宣言》之后、《联邦宪法》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于1777年11月15日在大陆会议通过,并于1781年3月1日生效。根据这个条例,“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在名义上又变成了“联合之邦”(United State)。这个联合之邦的名字,条例开宗明义地作了规定,叫“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 of America)。
三.在历史的岔路口上
现在,我们可以为美国的建国史大致列出一张时间表了:1754年以前,北美大地上已经有了十三个英属殖民地。1754年,他们开始联合。1765年,他们有了一个独立的新民族的概念(美利坚民族)。1774年,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和一个国家议会的雏形(大陆会议)。1776年他们有了一个关于未来国家的精神和理想(美国理想)。1777年,他们又有了这个国家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而且,从1774年开始,他们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互不相干的“英属殖民地”变成“联合殖民地”,其次是把“殖民地”变成“邦”,最后则是把“邦”变成“邦之联合”(邦联),进而变成“联合之邦”(联邦)。于是,美利坚人便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社会组织由“非国家”(殖民地)、“半国家”(邦)变成“国家”(美国)。
实际上,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既不像样子,又情况不妙。这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没有政府首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许多本应由政府来行使的权力(比如对外宣战、和约缔结、外交主导、货币制造),是由国会来行使的。国会的权力其实很小,比如组建海军、从各州招募军队、解决各州争端等,就需要三分之二邦的同意。这就难以巩固和发展独立战争的成果,无法有效抗衡西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英国人在海上的骚扰以及本国农民的起义,也实在承担不起诸如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之类的重任。原本松散脆弱的“联合之邦”,甚至面临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没法子,胜利之后分道扬镳的各邦,只好派出自己的代表,重新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制宪会议”的1787年费城会议。
不过,这次会议的任务原本不是制宪,与会各邦给代表们的训令也只是修改《邦联条例》。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就出在《邦联条例》上。1777年通过的《邦联条例》,是美国革命时期的产物,自然存在明显的草创性和过渡性,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是含糊其辞甚至含混不清的。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所谓“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结盟,还是高度自治地区的联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如果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构成这个国家的十三个State就是“州”,美利坚合众国就应该叫做“州联”(事实上也有人主张用这种方式来翻译United State)。相反,如果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则United State是国联:State也得理解为“国家”。可惜“州联”和“国联“的理解都不准确,因此我们只好把这时的United State称为“邦联”。
邦联不是国联,也不是联邦。也就是说,在邦联制度下,那些联合起来的 State,既不是国,更不是省,也不是后来联邦制度下的州,而是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邦联条例》明确规定,这些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领域与权利”,除非他们同意将这些权力和权利部分地授予邦联。所以,这个时候的United State of america(美国),还只是“邦之联合”(邦联),而非“联合之邦”(联邦)。组成邦联的State,也还只是邦,不是州。因此本文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在说到邦联时,称它为邦;在说到联邦时,称它为州。
但这样一来,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有些不三不四、非驴非马了。他们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四十三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在7月5日的会议上就说,事情难就难在“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其实是《独立宣言》留下的老问题。当《独立宣言》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时,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去说清楚,这究竟是十三个殖民地组成一个主权国家宣布独立,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相邀凑齐了一起同时宣布独立?不过当时并没有人计较这些。那时最重要的是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至于其他,也只能独立以后再说。
独立战争胜利了,而胜利后的国家状况并不那么理想,甚至充满危机。1787年费城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后来被称作“美国宪法之父”的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在他当年年初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信中说,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十三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麦迪逊显然是主张全面联合的。要实现全面联合,就必须有一个高于各邦政府的“全国最高政府”,更必须有一部高于各邦宪法的根本大法。因为只有这样一部法律,才能约束独立的各邦,并对新成立的“全国最高政府”授权。
这可不是修改一下《邦联条例》就行的。与会代表很快就发现,他们自己其实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邦联条例》进行其实无济于事的修改,要么另起炉灶,重新制定一个文件,即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幸而,在历史的岔路口上,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抛弃邦联制,实行联邦制,并为此制定一部《联邦宪法》。
四.走向共和
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堪称惜墨如金,一共只有七条。其中第一条讲立法,第二条讲行政,第三条讲司法,第四条规定各州(State)与联邦的关系,第五条规定修宪的程序,第六条规定宪法的地位,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
但在这个简洁的文本中,却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根据这一设计,国家权力既被纵向地分解为联邦的权力和各州的权力(其实是独立各邦部分让渡权力,变邦为州),又被横向地分解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其中,立法权属于美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而立法权又分属参、众两院。只有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法案才能成立。而且,总统对通过的法案有否决权,最高法院也可以判国会通过的法案“违宪”。虽然由实行终身制的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有裁决权,但大法官要由总统任命、参议院同意。总统虽然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但这一否决又可以由国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再否决。也就是说,这样,没有哪个人或哪个机构可以大权独揽,说一不二。
其实这正是制宪会议的难题之一。也就是说,既要把各邦的主权和权力收缴上来,交给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但又绝不允许这个政府是专制主义和君临天下的。
防止专制的惟一途径是分权,而制宪会议的目的却是要集权。在这里,美国的开国领袖们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们的办法是,既不集权于人(比如总统),也不集权于机构(比如国会),而是集权于法(宪法)。具体的说,就是用一部宪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邦或州(State,在宪法生效以后,我们将称它为州,不再称它为邦),都必须遵守而且不得违背这部共同约定的宪法。《联邦宪法》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或者将要缔结的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当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所有的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都应宣誓或作代誓宣言拥护本宪法。也就是说,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
美国以宪法为立国之本,用宪法来统一和治理国家,将立法、司法行政和各州权力都置于宪法之下,这就保证了集权而不专制。在宪法的统辖之下,各州(State),包括后来加入联邦的各州(现在已共有五十个之多),都享有充分的主权、独立和自由。他们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文字体系,自己的司法范围和法院系统,并按照自己的宪法由自己的人民选举自己的议员和官员,不受联邦政府的左右,只要不违背联邦宪法就行。很清楚,美国的五十个州,是用法(作为最高法律的联邦宪法)联合起来的。而且,联合之后,仍有相对的独立和高度的自由。
这就是共和了。共和之要义有三,一日公,二日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政权共享,和平共处”。“天下为公”并不是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将所有人的财产都收归公有,而只是确认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这就是“公”。正因为“公”(共有),才必须“共”(共享和共治)。既然是“共”,就不能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也必定并必须是和平的。这就是“和”。显然,所谓共和,就是因“公”(公共、公用、公众)而“共”(共有、共享、共治),因“共”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然而,要共和,就必须限政,即不能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政府或国会)独自坐大或者一统天下。所以,仅仅集权于宪法是不够的。如果对宪法的解释权和执行权集于一人或某一机构,就会变成宪政名义下的专政。因此,还必须在立宪集权的前提下立宪分权,通过宪法规定哪些权力属于哪些部门和哪些人。这就有了将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开来的“三权分立制”,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分别立法的“参、众两院制”。
这就是宪政了。宪政并不只是“宪政”(依照宪法行政),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行政)。它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因为作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国会如果不受限制,同样会造成专政,甚至更恐怖。这是一定要把国会分成参、众两院的意义。总之,必须最大限度地限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并让它们相互制约,这样才能防止它们单独或者联合起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公民的正当权利。
五.伟大的妥协
前面说过,没有大多数人的妥协,就不会有美国宪法。因为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他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十三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而要全面联合,就只有接受这部宪法。三十五岁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古文诺·莫里斯的最后发言很能说明问题。古文诺·莫里斯说,他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大多数人已决定赞同,自己也应该受此决心的约束。他强调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有一个全国政府,那就只好签字。
我们知道,古文诺·莫里斯是制宪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他是这次会议上发言次数最多的一个人,共发言一百七十三次(其次为同一个邦的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一百六十多次;再次为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一百五十多次)。而且,由于他文笔精巧细腻,宪法文本最后主要是由他来定稿的。这样一个人都对宪法草案不满,何况其他?
古文诺·莫里斯发言后,平时很少发言的三十七岁的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接着表态。威廉·布朗特说他曾宣布过自己不会签字,也不愿意以誓词支持这个方案,但也不想使自己妨碍大家的意愿,这就是:这个方案是制宪会议上各邦的一致行动。这其实也是古文诺·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共同想法,即不管怎么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不能分裂,十三个邦应该一致行动。
不过,方向的一致不等于方案的相同,更不等于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当方案涉及各自利益时,那就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致制宪会议好几次差一点不欢而散。八十一岁高龄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甚至提议聘请一位牧师,在每天开会前主持祈祷,恳请代表们放弃“惟有自己正确”的观念。事实上,正是由于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冷静理智的态度,居中调解的一方又能提出合理的建议,制宪会议才从走投无路转向柳暗花明,并最终达成协议。
比如国会问题。
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一个联邦议会,这一点大家并无分歧。问题是国会如何设置如何组建,席位如何分配如何安排,制宪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提出和赞成《弗吉尼亚方案》的人坚持民主原则,主张实行两院制,其中第一院(众议院)议员由选民选出,第二院(参议院)议员由第一院议员选岀,两院席位都按各邦人口比例分配。而提出和赞成《新泽西方案》的人则坚持共和原则,主张实行一院制,席位按邦分配,每邦一票表决权。
不过,冠冕堂皇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的驱使。主张按比例的,主要是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和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他们代表大邦的利益。主张讲平等的主要是新泽西代表威廉·佩特森和特拉华代表刚宁·贝德福德。他们代表小邦的利益。小邦代表坚持认为,大邦的意图就是要吞噬小邦,因此他们扬言宁肯投靠外国,也决不亡于大邦。大邦代表也不让步,甚至连剑与火、绞刑架之类的话都说出来了。幸亏这时康涅狄格代表奥立维·艾尔斯沃斯等人出来调停。他们代表中等邦,可以不偏不倚。在他们的斡旋之下,制宪会议于7月16日达成妥协:众议院实行国内法原则,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照顾大邦;参议院实行国际法原则,不论大小,每邦一席(后改为两席),照顾小邦,尤其是特拉华和罗德岛。
这次妥协后来被美国宪法学家称为“伟大的妥协”。这倒不光是因为它帮助制宪会议走出了僵局,而且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民主原则与共和原则共存的成功范例。众议院民主,参议院共和,两大原则共存于国会,岂非一种比单一共和制度更高境界的共和?
其实妥协是一种政治美德,因为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共和。至少,它也是走出困境的一种方法。对此,富兰克林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在6月30日的会议上说,木匠做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匀,他就会两边各削去一点,让连接的地方严丝合缝,桌子也就平稳了。现在,我们这艘船为大家所共有,难道不该由大家来共同决定冒险的规则吗?
富兰克林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六十四岁的康涅狄格代表罗杰·谢尔曼说,没有人愿意就这样一事无成地散会。六十二岁的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更是情绪激动。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如鸟兽散,陷国家于不堪。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多代表(主要是大邦代表)决定妥协,以保证邦联不会分崩离析。
六.最不坏的就是最好的
妥协保住了草拟中的宪法,宪法也体现了妥协的精神。事隔多年,当我们蓦然回首,重新审视这部宪法时就会发现,妥协并不仅仅只是制宪代表的权宜之计,它也是制宪工作的思想方法。那些取得了制宪会议高度一致的看法,就写成宪法中的刚性条文;那些取得大致相同意见的观点,就写成宪法中的柔性条文;那些达成初步共同意向的部分,就留下今后继续发挥的余地;而那些实在达不成统一的问题,则干脆只字不提,暂付阙如。因此美国宪法虽然二百多年来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却又有一系列的“修正案”,而且几乎从它批准之日起就有了。二百多年后,美国人民仍很感激先辈们的妥协,并庆幸他们不是“完美主义者”,庆幸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能有这样一个观点: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
这个观点也是富兰克林博士提出来的。他在9月17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深情而智慧的书面发言,并由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代为宣读。富兰克林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自己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因此,无论召开多少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从这种感觉出发,富兰克林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实是瑕疵的话。他也希望其他代表略为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并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来自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古文诺·莫里斯赞同富兰克林的观点。他说自己对宪法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这已是目前达到的最佳方案,愿意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
在威尔逊宣读完富兰克林的书面发言后,三十四岁的弗吉尼亚代表爱德蒙·伦道夫接过话头,起立对自己拒绝签字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尽管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姓名都对宪法的智慧和价值表示嘉许,但他自己却仍然只能受责任心的支配,等待未来的裁决。当富兰克林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爱德蒙·伦道夫,希望他暂时把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和自己的兄弟们采取一致行动时,爱德蒙·伦道夫回答说,拒绝在宪法上签字,也许是自己一生中最坏的选择,但良知迫使自己这样做,不可改变。我们知道,爱德蒙·伦道夫不是等闲人物,他是制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正是他,作为会议的第一位正式发言人,向代表们陈述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和意义,其代表弗吉尼亚提出的制宪方案甚至又称《伦道夫方案》。他以揭开会议主题开始,却要以反对会议决议告终,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爱德蒙·伦道夫说完后,四十三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也站起来,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艾尔布里奇·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款》上签字,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心里当然不会好受。何况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艾尔布里奇·格里也是全身心投入讨论的。所以他表示,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自己不会采取拒绝签字的方式来表示态度,但现在已逼上梁山,却别无选择。
七.限法之法才是法
乔治·梅森是弗吉尼亚代表。他是一个农场主,有三百多名奴隶,但他本人却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他曾经参与制定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权利法案”,从而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十三个邦的宪法中惟一具备权利条款的宪法。对于他来说,权利法案比什么都重要。此外,很多人对联邦宪法缺少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都不满。曾执笔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公干,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大声疾呼要进行弥补。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在看到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寄给他的联邦宪法文本后,也指出了缺少权利条款的这一缺陷之处。拉法耶特侯爵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曾在华盛顿的麾下当一名少将。他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写第一稿),可谓“两个世界的英雄”。
那么,如此重要的条款怎么没有写进宪法呢?在这一点上,“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并无分歧。在前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坚强之全国政府”,以免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陷入内乱、分裂和无政府状态。因此,费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在1787年,大多数的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明确保障了个人权利。而现在要做的,是对联邦政府授权。只要明确联邦政府的权限,它就不能做未经授权的事情。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被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这岂不是更糟糕?在美国人民看来,“个人权利”比所谓“国家利益”和“政府权力”更重要。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而人民则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也就没有人民授权的国会和政府。而且,人们之所以要建立政府,正是为了保障每个个人的这些权利。这正是《独立宣言》的精神,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精神。因此,许多邦(比如马萨诸塞)的议会在通过联邦宪法时,其决议都附上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
联邦主义者同意了这一条件,力主增加这些条款的乔治·梅森也因此被看作是“权利法案之父”。于是,第一届联邦议会就有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这些法案分别列举了民众个人的一系列权利,声称这些权利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保障,是政府和国会不能蚕食、侵犯、剥夺的。尔后,美国国会于1789年9月25日通过了这十条宪法修正案,将其作为美国宪法的补充条款,并于1791年12月15日得到十一个州(这时它们应该叫做州”而不是“邦”了)的批准,开始生效。这十条法案通常称作“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在第一修正案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简言之,它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
这样一来,不但行政机关要受到限制,立法机关也要受到限制。于是,就可以看出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却是限政。在宪政主义者看来,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民主和道德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得住的只有宪政。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它的任务,是把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的权力都尽可能地限制在不会侵犯公民权利、不会导致专政和暴政的范围之内。
联邦宪法其实已经体现了这一精神,比如三权分立,比如两院立法,比如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相互制衡等等。但美国人民还强烈要求自己的宪法必须明文规定,即便通过法案的条件完全具备——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统不否决,最高法院也不判其“违宪”,某些法案仍然不能成立,甚至不能考虑。
二百多年前那场争论,终于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方式做出了结论,但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却仍然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在这一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宪法正文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而在诸法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第一修正案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则是: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人民是第一位的;而在人民之中,个人是第一位的。这两种原则和思路看起来似乎相反,其实一致。因为第一种原则和思路中所说的“人”,是指议员、官员和法官。他们实际上是“国家”(政府)。国家必须服从宪法,而宪法之所以高于国家,则因为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公民是第一位,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是第二位,保障公民和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是第三位,由宪法派生的法律是第四位,由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会、行政机构和法院是最后一位。这就是美国人建国的思路和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独立宣言》的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