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在广东东莞大街小巷或厂房林立的工业区里,包括电子、皮革、缝纫、玩具厂在内的各类型的工厂都在招聘。需要10人,通常招20人。许多工厂降低年龄要求,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就行。工资也涨到每月5000到8000元,“上不封顶”。据专做东莞工人中介服务的王超介绍,目前进厂的打工者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只要肯干,先拿四五千块钱一个月,边干边学,等到当上技工师傅就能有个七八千块钱,前提是熬得住。“只要员工在工厂能待10天以上,我的中介工作就算成功,但就算是这样,我经手的新员工进厂能干满10天的,还不到60%。”他说。年轻人越来越不爱进工厂,甚至正在逃离工厂。他们的选择有很多,送外卖、快递员,甚至回到老家开个小店。刘文平进厂打工已有8年,多次逃离又多次回去。挣钱只能靠加班,经常一两个月没有休息。在不断重复的工作里,他没有任何成长,意志越来越消沉。为了想挣脱这样的环境,几乎每干半年,就会离开工厂。
刘文平从2013年来到东莞,在工厂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过外卖、做过中介,还做自媒体。摄影:张楠茜
在他们看来,工厂招不到人的根本原因还是待遇和管理问题。但是一些工厂宁愿长期空岗,也不愿意改变,旺季大量招人,淡季就辞退工人。红色的水桶里塞满棉被,鼓鼓囊囊冒出来,水桶下垫着黑色行李袋,一起坐在小推车上。程波左手拉推车,右手推着一个及腰高的41寸行李箱,停驻在东莞虎门镇博头路的一家制衣缝纫厂门前,盯着卷帘门上的招聘信息,搜寻“临时工”三个字:“招临工,计件,月薪5000到10000元,上不封顶,包吃住。”程波左手拉推车,右手推着及腰高的41寸行李箱,停驻在东莞虎门镇博头路的一家制衣缝纫厂门前,盯着卷帘门上的招聘信息。摄影:张楠茜程波是一名车位缝纫工,一直在找工作。他走进这家工厂,偌大的车间,上百台缝纫机只有不到十个工人在工作,缝纫机不停地发出嘎嘎的刺耳声音。一位女工告诉程波,去年疫情后,很多人就没有回来工作了。她把两片布块对齐放进缝纫机里,线轴上下转动,将丝线整齐细密地扎进衣服。缝制一件公主裙,要完成抽褶、缝合、卷边三道工序,主管给出的计件工资是每件1元5角。程波摩挲面布、面纱、里布,考虑是否要留下。车间温度高,汗水浸湿他的后背。主管戴着口罩,眼神里却写满了不耐烦。程波最终没有接下这份工作,提桶走了。“看一个工厂好不好,要看工作的人多不多,领导好不好。这里做裙子的工序复杂,1块5的价格有点低了。”程波是一名车位缝纫工,偌大的车间,上百台缝纫机只有不到十个工人在工作,缝制一件公主裙,计件工资是每件1元5角。摄影:张楠茜这已经是两天半的时间里,程波面试过的第十份工作。他在上一家工厂做满一个月,结算工资的时候才发现工价被主管降低了,少拿了3000块的工资。因为怕重蹈覆辙,他找工作变得小心谨慎,而且只想找临时工。“只要尝试做过临时工,没被坑过的,都会选择去做临时工而不是正式工。”王超在东莞经营着一家名为禾汇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劳务中介,他很能理解程波。他现在主要做临时工的服务,“一是方便结账拿钱走人,二是不用像正式工那样押一个月的工资。”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再多待一天,吃住又是花销几十块,程波直接去火车站,坐车回老家了。这次离开奋斗过十来年的广东,他不会再回来。“要提最红的桶,大吉大利。”东莞的打工娃刘文平说,他也离开工厂半年了,并且决定不再进厂。据去年的《东莞市制造业人才发展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东莞,有超过420万人从事制造业,无论是在钢筋森林的大型工业区,还是藏于巷子的小型作坊,工厂每天都在招工,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进厂。一些人也像程波、刘文平那样,选择逃离工厂。水桶是每个工厂娃的必备品,他们把离开工厂戏谑地叫做“提桶跑路”。刘文平身高1米6,圆脸、小眼睛、厚嘴唇,来自贵州山区,说普通话不分平翘舌和前后鼻音。他从2013年来到东莞,在工厂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过外卖、做过中介,还做自媒体。现在他住在东莞一个月230元的出租屋里,每天吃饭、睡觉、上网,对未来很迷茫。他今年28岁,中学毕业、职高辍学,进厂8年,从电子厂的普工干到印刷厂的机器师傅,月薪从3000元到8000元。其间,他提桶跑路9次,在每一家工厂最多三个月、最长不过一年。在中介王超看来,能在一家厂里待够三个月的刘文平,已经算踏实。频繁提桶跑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工厂的常态。东莞街头随处可见招聘信息,工时费普遍在15元到19元每小时。摄影:张楠茜今年春节后,王超16岁的侄子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从老家重庆到东莞打工,王超负责给侄子找工作。侄子一个月就换了十几个厂,每个厂干两天就离开。他服务的一个21岁的广东小伙,4月初进厂工作仅一周,就找王超借了两百块,然后离开工厂,失联了。王超发现,因为年轻工人的不断流失,一些大的工厂工人断层严重,班组工人编号从一千多号,一下就到四五千号——中间是走掉的,前面几个是十几年的老员工,后面的就是从技校合作签来的学生工。最底层的“白菜价”的学生实习工是目前最好招的,每年的暑假,大批从技校来的学生工,被一辆辆的大巴车拉到工厂,他们每天固定工作10个小时,从早晨7点做到晚上8点,一个月不休息,到手还不到4000块钱。“现在年轻人都比较浮躁,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如果没有班上了,一打父母电话,借点生活费,又过个几天。”王超说,很多工厂里只剩下两类人,一是来了刚出社会寻求过渡的年轻人,干几个月就走;二是已经结婚的三四十岁的,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失业,进工厂求的是稳定。2012年,刘文平初中毕业。他在家中排老二,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因为家里贫困,大哥中学毕业就出门打工,把机会让给弟妹。刘文平成绩不好,也没有继续读高中,问母亲要了1000块钱,第一次坐火车到重庆,去了万州的一家职业学校读书,想着将来可以靠打工供自己读书。读了半年,刘文平却发现在这家职业学校完全学不到知识或者技能。身边同学都是因为成绩不好才来的,天天打架抽烟混日子,不仅没有学习氛围,考试还被老师鼓励花钱买答案。每一届学生毕业,都被学校安排进工厂打工,学校还收取中介费用。2012年下半年,刘文平进入一个日本马达工厂勤工俭学。他在流水线上做测试工作,工价是每小时9元5角,一个月的工资到手2000多块钱。他想着,既然迟早都是干流水线,何必费劲读几年书,于是直接辍学,去了哥哥在的东莞找工作。2013年,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是1310元一个月,这也是东莞绝大多数工厂的底薪。彼时,东莞已经是全世界电子制造业最大基地,号称“东莞塞车,世界缺货”,电子厂是很多学历不高、又没技术的年轻人的进厂首选。刘文平也跟着老乡一起,进了一个电子厂当普工,负责组装手机屏幕上的亮度灯。一个小时10元钱,两班倒,白班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他第一次体会到“站着都能睡着”。东莞打工者租住的宿舍,外观已经颇为破旧。摄影:张楠茜传送带不断运输零件,刘文平双手机械地重复组装,耳朵里是无休止的机器轰鸣声,他觉得大脑空白,手练到条件反射。一天工作10个钟头,没空和旁人交流,照做、执行,他跟着传输带一起,仿佛一起成为一个机器。在工厂里,所有时间都被严格切割。早8点到晚8点,每2个小时休息10分钟,中午12点到1点是吃饭时间,有的工厂大,车间离食堂远,跑得慢,到了食堂还要排长队。吃完饭回到车间,趴在机器上或者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又要接着开始干活。工人上班是白班、夜班两班倒,流水线则是日夜不停,夜班要通宵,加5块钱,不愿意干就得走人。每天都很累,回到宿舍只想躺着。上班时间要上厕所,就要请线长来顶上。一条线十几个人,只有一个线长,所以工人上厕所也要小心翼翼。小号5分钟,大号10分钟,每个人有次数限定,并且要登记在本子上。干了不到一年,刘文平提桶跑路。他想找别的工作,但是学历拿不出手。从工厂里出去,他还是像刚毕业的中学生进入社会一样,什么也不会,整个人没有自信,比以前更加内向,找不到比工厂工人更好的工作。眼看着钱快花完了,刘文平又进入一家电子厂,干了一年。2016年,他再次提桶跑路,换去了一家印刷厂做普工,每天插充电器的纸盒子,还是像以前的电子厂一样,做机械的重复性工作。在工厂里,老板用upph(单位人事产能)来衡量员工工作绩效,充斥着比速度的氛围,直到达到人的极限。刘文平每天折上万个装充电器的纸盒子,手指磨得起了水疱,他仍然不断调整拇指方向、胳膊幅度,希望能加快速度。“但你干活的手速快,流水线调的速度更快,你闷着干,领班也拼了命地催。”一切都没有尽头。他要和自己比,前一天做了9000个,第二天就要做10000个;要和同事比,如果有人做得更多,就要超过旁人。每天晚上,线长都要开会做总结,不留余地地当众批评做得慢的工人。刘文平虽然没有被坑过,但一些朋友告诉他,发工资的时候和最初的预期差别很大。虽然很多工厂招聘写着,普工月薪3500元至9000元,组长月薪4000元至10000元,上不封顶。但老板会找各种理由克扣工资,比如迟到、不参加团建、业绩或者表现不好,一扣就是上百块。干了一个月,有人明明算的工资有8000块,到手却不到一半。一些人不断离开工厂,“除了一堆游戏装备皮肤和会员卡,一身伤病,仅剩的住房公积金,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情感,什么都没有。”一位离开工厂的人这样写道。刘文平在印刷厂干了一年,又离开了。他每次走,都下定决心不再进厂。但是最后钱快花完了,找不到别的工作,还是只能回到工厂。“其实干流水线没有不苦的,不只是身体的苦,更大的苦是看不到希望。很多人想跳出工厂,却没有方向。”刘文平这样总结自己的工厂生活。他刚来到东莞时,想要出人头地,但进入工厂,一眼就看到生活的尽头——厂子里有人做了一辈子,升到线长、组长,工资就比员工高几百块。不仅如此,他们因为常年熬夜、重复机械工作,黑眼圈深重,有人年纪轻轻就头发花白、活力尽丧。刘文平很害怕自己以后也会成为那样,他开始寻求出路。用进厂第一个月的工资,他买了台电脑,学会电脑的基本操作,还有平面和动画设计、网站建设、基本的视频照片处理技术……他搭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网站,在上面写写自己的工厂生活,顺便结交一些朋友。后来,刘文平又开始做优化网站,做seo(搜索引擎优化)排名、挂广告赢利,帮一些小工厂创建网站、收取费用。2015年,他最多同时做过十几个网站,可以依靠这份兼职,离开工厂过生活。但没过多久,他的网站就遭到攻击,导致广告联盟封禁账户,收入又变得不稳定,他不得不再度回到工厂。在厂里,他也遇到过很多努力的人。有一个在工厂多年的工友每天都干活积极,甚至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也在干。后来厂里线长的职位空缺,他以为自己能上,却由一个刚进厂的、和组长关系好的年轻人顶上了。工友一蹶不振,干活儿也慢了,组长开始因为各种小事找他茬,他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刘文平看过太多普工被淘汰的例子,于是他努力从普工干到了技术岗位。进入一家印刷厂后,老乡把他从流水线调到机台上做学徒。一个工厂往往只有一两台机器,对应一两个师傅。师傅教会徒弟师傅就会被淘汰,所以除了关系好的,师傅一般不会教人。刘文平一开始在旁边偷偷学,下班的时候整理好材料、调好机器,师傅上班了直接操作,他就有机会跟着学。时间久了,师傅看他勤快,也愿意说几句。别人一个月就学会的机器操作,刘文平学了几个月,终于在2017年能够操作机器了。他提桶跑路换了个厂子,成为操作机器的师傅。这时候,他已经能拿到8000多一个月的工资。新进的印刷工厂,却在半年里就倒闭了。这家印刷厂原本是一家小厂,老板接到一个大订单,于是扩大规模,买入新设备,员工也从几个人增加到十几人,但很快就因为资金周转不开,只能裁员,先裁掉做饭的阿姨,换成老板的老爸来做饭,然后裁掉普工,最后就到了操机师傅刘文平。在离开工厂后,刘文平送过外卖。但意外不断,有时候剐蹭到别人的车,有时候车被交警扣了。送外卖成为一些不愿进工厂的年轻人的选择,但这条路并不好走。图为东莞市街头的外卖员。摄影:张楠茜有一次凌晨送餐赶时间,加上路灯昏暗,他一个没注意,连车带人栽进了坑里,手掌和胳膊都擦出了血,送的饮料洒了一地,烧鸡摔出去老远。按照外卖平台的规定,他只能自己赔钱。小伤舍不得去医院,刘文平回家清理伤口,为了减少些损失,他把摔坏的外卖吃了,边吃边苦笑。前些年,他靠打工存了一些钱,听一位网友的建议,买虚拟币和资金盘,每个月都投工资进去,却遇到诈骗公司,40000多元的积蓄全亏了。因为没钱,他三年都没脸回家,也不敢告诉父母。去年国庆节假期,刘文平终于回家了,他一边装修家里的老房子,一边和一位带孩子的离异妇女相亲,却被对方拒绝了。“普工一个月4500-5000块,只要能做就行,50来岁的都接受。”这是彭晓军的鞋厂开出的招聘信息。他的鞋厂位于东莞道窖工业区,北靠广州,成立十几年,主要做鞋底的橡胶和中底工序。彭晓军记得,十多年前,两三千元的工资招年轻人根本不是问题。那时候,沿海城市的市区居民90%的人都是工人子弟,年轻人要想进个好的工厂,还得托熟人请客送礼;一些大工厂有各种面试考试,对性别、年龄,甚至是省份和民族都有要求,还有些厂连染发、文身、指甲长的员工都不要。2014年左右,东莞出现招工荒,一些厂子虽然调高了工人工资、更换厂址,但用工荒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一直没有改善。现在,每天都有朋友的厂子倒闭消息传来,彭晓军感叹老板不好当。他的厂子里,一共有100来号工人,员工基本上都是40岁上下的,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稳定。然而,这些老员工奋斗的动力,就是子女不要再进厂当工人。“家里就一两个小孩,都是宝贝。所以小孩都不想进厂,有的来了干几天,一两个月就走了。”彭晓军工厂的行政主管说,他家里也只有一个孩子,不会愿意让孩子进工厂。去年疫情,订单和收入都不稳定,彭晓军的工厂没有更新设备,但今后用机器替换人力是必然的趋势。通常来说,一台机器几十万元,能取代两个熟练工,原来两个工人要做一天的量,一台机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而为了招到人,像彭晓军这样的工厂管理人员,越来越倾向于和用工中介合作。中介夹在工厂、工人中间,更能瞥见结构性招工难下,一些难以调和的问题。东莞街头随处可见招聘信息,工时费普遍在15元到19元每小时。摄影:张楠茜上文提到过的王超的中介公司,就属于分包公司。一边,王超把工人对接到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公司签有多家工厂,哪里缺人就送哪里去;另一边,他跟员工签临时协议,约定做满工期,按工价拿工资。工人每小时的工作,中介都能拿到提成。当中介从工厂或劳务派遣公司接单出来,比如工厂本来给20元一个小时,转几手,中介抽一元或五角,劳务派遣公司再抽去一点,层层分包,到工人手里可能就是17元一个钟。入行近四年来,王超见证了成百上千次提桶,离开和回来。有人从他一入行就跟着他干,稳定地能在一个工厂干上一年多。也有“三和大神”类似的人,对方没有微信,没有手机卡,平时从来不和他联系,等到发工资的那天,会想尽办法找个地方连上Wi-Fi,用支付宝发消息要工资,2000块钱可以用半年。王超认为,工厂不是招不到人,而是舍不得提高待遇,缺少熟练工和苦工种。“比如,虽然招聘启示上写着每月工资8000元,但实际上到手就四五千块。又比如,员工提意见,每天到晚上一两点的加班时间太长了,你工厂不改,哪怕临时工去了也会走。一些厂子一个小时只给14块钱,别人给18块钱,那肯定工人要去18块那里。”虽然年轻人不好安排了,但王超并没有感觉到用工荒,新生劳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地来到东莞。在接受采访期间,一个微信语音电话匆忙打进来,是4月初不辞而别的广东河源小伙。他从工厂离开失联近一个月,现在突然又回来要找工作,还带来两个朋友,一个是2003年出生的弟弟,一个是还没满16岁的表妹。他希望王超帮他找找关系,三人一起进厂。年轻人寻求机会进厂的时候,刘文平则在4月底又回到贵州深山里的老家。因为父母都不识字,也不会挂号,他要带着腿脚疼痛的妈妈,去七八十公里外的县城医院看病。他想着,忙完这一阵,还会回到东莞,也许会到工厂区附近开个贵州羊肉粉店,再试试能不能不进厂也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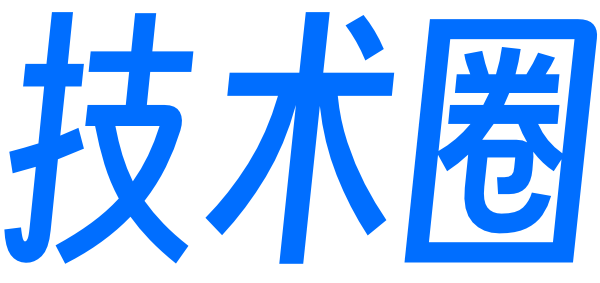 下载APP
下载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