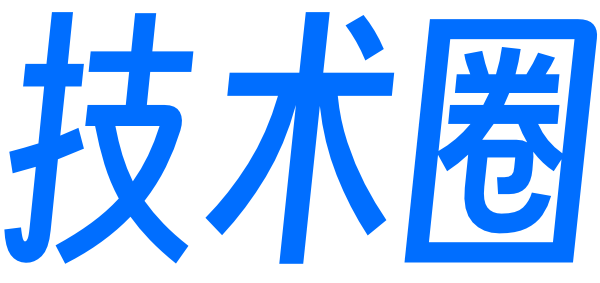交大ACM班:俞勇和他的天才少年们
20年前,上海交通大学用三天时间做了一个决定:成立ACM班。
而这,直接推动了此后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ACM班也在后来被冠以“人工智能CTO摇篮”的盛誉。
提出这个设想的创始人是当时刚刚年过四十的俞勇。
铸魂励志:
从ACM冠军到ACM班
2002年6月16日,担任上海交通大学ACM国际大学生设计程序竞赛(ACM-ICPC)总教练六年后,俞勇很早就在心中许下的夙愿终于开始迎来曙光:培养属于中国自己的计算机科学家。 这一天,俞勇找到主管学校教学的校长,提出要在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ACM班的申请。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重大决定,俞勇在隔天的18日就得到上海交大的批复。 更何况,当时,国内尚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供借鉴的参考,众所周知的清华姚班也是在三年后(2005年秋季)才发布招生计划。 但是,你更难想象的是, 三天批复的背后,是俞勇六年,甚至二十余年的积淀。 俞勇之所以能这么快得到批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一年的三月份,交大学生林晨曦、陆靖、周健组队,代表中国获得了第一个ACM-ICPC的冠军。 而俞勇的教育情结则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以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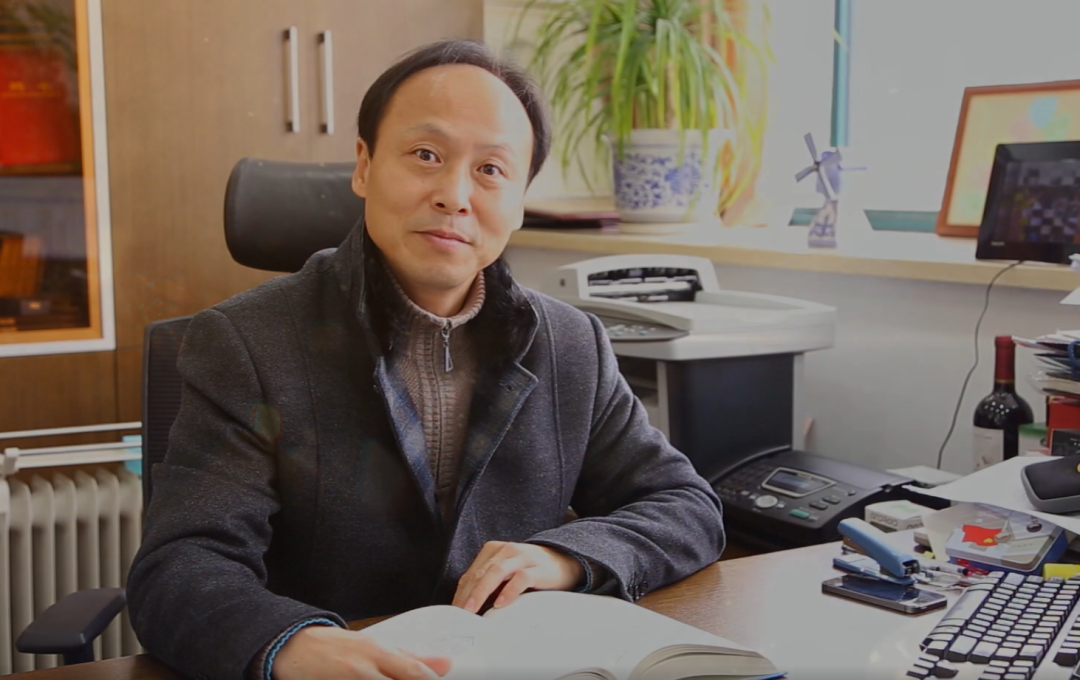 俞勇
从小就想当老师的俞勇大学选择的是知名教育学府华东师范大学。在这里,有两个人对俞勇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个就是时任华师大校长刘佛年。在当时的开学典礼上,刘佛年讲,做老师不光要教好书,还要懂教育。
当时的俞勇还没有深刻理解教育这两个字的意义,但他明白从教书到教育必然不一样。也是这时起,俞勇就立志要做一名教育家。
另一个让俞勇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的华东师大计算机系主任张东韩。
有一天,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一场报告会,讲者正是张东韩。这场报告说不上多么隆重,但却被台下的俞勇铭记了许久许久。
那天晚上,台上的张东韩滔滔不绝;台下的俞勇沉浸其中。
时至今日,俞勇已经记不起那场报告的主要内容,但对于当年的情形却仍然如数家珍。
“没有讲台,就一把椅子对着学生,他坐在台前。”俞勇如此回忆道,“讲什么内容没有太清楚,但是那种儒雅学识的大师风范,是忘不了的。”
这次经历,让本就身在师范大学的俞勇更加坚定了对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追求。
1986年,从华东师大硕士毕业以后,俞勇选择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名老师,至今已经三十六载。
在交大,俞勇最早的工资是128元,数年未变。同时期,外企的工资却已经以千计算,2000元几乎已经是底线。
这也使得,俞勇的耳边一直不乏让他放弃交大的声音,但俞勇始终不为所动。而他的机会,终于开始渐行渐近。
1996年,ACM-ICPC进入中国,俞勇成为最早组建队伍参加比赛的人。
然而,成功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
即使到2002年,一番“神”操作下,命运之神眷顾了他们,俞勇开创了历史,ACM班顺利成立。而这背后,是一群天才少年的精诚协作。
前文已经提到,帮助交大获得世界冠军的三名学生分别是陆靖、林晨曦和周健。
如今的林晨曦,已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明星公司,依图科技的联合创始人。
但林晨曦最初并不是计算机系学生,学的是现在常常被人调侃为“四大天坑”之一的材料专业。
俞勇在选拔ACM队伍的过程中,意外挖掘出林晨曦这个人才,而林晨曦终不负所望。
在俞勇看来,林晨曦行事稳重,头脑清晰,全局观念强,适合做队长。
“他脑子特别清楚,不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是个成大事的人。”彼时,俞勇就做出这样的判断。
这从林晨曦重读一年计算机专业课也可以看出。
依林晨曦的水平,虽是转了专业,但无需重读。很多学生往往会不得已才重读,林晨曦则选择主动重读一年。
“我们得不到冠军,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不敢想。”在夺得冠军后,林晨曦多次在队员面前提起这句话。
为了证明这句话,他决定以晚一年毕业为代价,全力追逐ACM-ICPC冠军这个梦想。
相比之下,陆靖倒是更像意气风发的天才。
2000年,陆靖还不曾参加比赛。但当他看到同学拿回来的题,却满眼都是光,“这些题目我都会做啊。”
“陆靖是个天才。”陆靖的出现让俞勇惊喜不已,他知道自己挖到一个宝,但对于如何让这个宝充分发光,其实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对于林晨曦是否继续参加比赛,他们犹豫了。
ACM比赛每个人只能参加两次,机会并不多。最终,林晨曦被安排等待2002年的比赛。
原因是,尽管陆靖很厉害,但第一次参加总决赛还是觉得有些担忧。
结果,陆靖被派去参加了2001年的ACM-ICPC,真就名落孙山。
但这次经历让陆靖明白一个道理:ACM-ICPC是一个团队比赛,个人实力再强,一个人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转年以后,才有了林晨曦、陆靖再带上他们的师弟周健,组队比赛,捧回ACM-ICPC的世界冠军。
对俞勇来说,冠军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俞勇获得了自由发挥的机会,以此为契机成立ACM班,开启了交大此后二十年间在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领域的传奇故事。
“冠军不是我的目的,我觉得拿到冠军以后,我有这个筹码可以让学校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2019年,俞勇在和雷峰网交流时这样说道。
确实,正是俞勇心中的这颗火苗被不断点燃,才有了本节开头的事情:俞勇如愿成立了ACM班,此后二十年间,培养了戴文渊、李沐、陈天奇、李磊、郑曌等一大批人工智能领域大神级人物。
当然,从这里走出也不止有“人工智能大师”。2018年,一名ACM班的2004级学生在辗转多年后,终于成了哈佛医学院的教师;
而在学术研究之外,ACM学生还参与创立了一批知名公司,包括饿了么、依图科技、第四范式、森亿智能、流利说、触宝科技......
而这正源自于ACM班独特的文化。
无论是林晨曦经常提在嘴边的“敢于想象”,还是陆靖领悟到的“团队合作”,都是ACM班文化的一部分。
但对俞勇来说,ACM班文化的核心是“超越”:他希望以ACM竞赛为契机,探索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让一群有天分的少年实现“超越”。
不仅在大学的时候能取得好的成绩,更要让他们在更长的人生中,走得更远、更稳。
正如古人云: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深谙此道的俞勇,对于学生的要求远不止于专业课,尽管他在为ACM班寻找最优秀的授课教师上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
在他看来,学好专业课是一个学生的本能,一定会重视,而专业外的能力,对他们来说这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
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俞勇本人唯一负责、ACM班独有的课程“学子讲坛”上:在这门课程中,俞勇不是绝对的主导者,每一名学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内容方面,讲的则是非计算机类的文学时政方方面面。课程分四学期,每名学生一学期讲一次,主题素材均自定。
这门课程尽管不是专业课,但和雷峰网交流的多位ACM班学生们均表示,如果要选一门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课程,那绝对是“学子讲坛”。
另一门类似的课程是“教学实践”。这是一门必修课,每个ACM班的学生,都需要在本科四年里完成至少一次低年级的课程助教。通过高年级学长与低年级新人的互动,将ACM班的传统一代代传下去,形成良性循环。
如此种种,不仅让学生们理解了梦想与追求、责任与担当、感恩与包容,更是从一支冠军队开始,铸造了ACM班这个真正优秀的团队。
俞勇
从小就想当老师的俞勇大学选择的是知名教育学府华东师范大学。在这里,有两个人对俞勇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个就是时任华师大校长刘佛年。在当时的开学典礼上,刘佛年讲,做老师不光要教好书,还要懂教育。
当时的俞勇还没有深刻理解教育这两个字的意义,但他明白从教书到教育必然不一样。也是这时起,俞勇就立志要做一名教育家。
另一个让俞勇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的华东师大计算机系主任张东韩。
有一天,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一场报告会,讲者正是张东韩。这场报告说不上多么隆重,但却被台下的俞勇铭记了许久许久。
那天晚上,台上的张东韩滔滔不绝;台下的俞勇沉浸其中。
时至今日,俞勇已经记不起那场报告的主要内容,但对于当年的情形却仍然如数家珍。
“没有讲台,就一把椅子对着学生,他坐在台前。”俞勇如此回忆道,“讲什么内容没有太清楚,但是那种儒雅学识的大师风范,是忘不了的。”
这次经历,让本就身在师范大学的俞勇更加坚定了对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追求。
1986年,从华东师大硕士毕业以后,俞勇选择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名老师,至今已经三十六载。
在交大,俞勇最早的工资是128元,数年未变。同时期,外企的工资却已经以千计算,2000元几乎已经是底线。
这也使得,俞勇的耳边一直不乏让他放弃交大的声音,但俞勇始终不为所动。而他的机会,终于开始渐行渐近。
1996年,ACM-ICPC进入中国,俞勇成为最早组建队伍参加比赛的人。
然而,成功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
即使到2002年,一番“神”操作下,命运之神眷顾了他们,俞勇开创了历史,ACM班顺利成立。而这背后,是一群天才少年的精诚协作。
前文已经提到,帮助交大获得世界冠军的三名学生分别是陆靖、林晨曦和周健。
如今的林晨曦,已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明星公司,依图科技的联合创始人。
但林晨曦最初并不是计算机系学生,学的是现在常常被人调侃为“四大天坑”之一的材料专业。
俞勇在选拔ACM队伍的过程中,意外挖掘出林晨曦这个人才,而林晨曦终不负所望。
在俞勇看来,林晨曦行事稳重,头脑清晰,全局观念强,适合做队长。
“他脑子特别清楚,不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是个成大事的人。”彼时,俞勇就做出这样的判断。
这从林晨曦重读一年计算机专业课也可以看出。
依林晨曦的水平,虽是转了专业,但无需重读。很多学生往往会不得已才重读,林晨曦则选择主动重读一年。
“我们得不到冠军,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不敢想。”在夺得冠军后,林晨曦多次在队员面前提起这句话。
为了证明这句话,他决定以晚一年毕业为代价,全力追逐ACM-ICPC冠军这个梦想。
相比之下,陆靖倒是更像意气风发的天才。
2000年,陆靖还不曾参加比赛。但当他看到同学拿回来的题,却满眼都是光,“这些题目我都会做啊。”
“陆靖是个天才。”陆靖的出现让俞勇惊喜不已,他知道自己挖到一个宝,但对于如何让这个宝充分发光,其实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对于林晨曦是否继续参加比赛,他们犹豫了。
ACM比赛每个人只能参加两次,机会并不多。最终,林晨曦被安排等待2002年的比赛。
原因是,尽管陆靖很厉害,但第一次参加总决赛还是觉得有些担忧。
结果,陆靖被派去参加了2001年的ACM-ICPC,真就名落孙山。
但这次经历让陆靖明白一个道理:ACM-ICPC是一个团队比赛,个人实力再强,一个人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转年以后,才有了林晨曦、陆靖再带上他们的师弟周健,组队比赛,捧回ACM-ICPC的世界冠军。
对俞勇来说,冠军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俞勇获得了自由发挥的机会,以此为契机成立ACM班,开启了交大此后二十年间在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领域的传奇故事。
“冠军不是我的目的,我觉得拿到冠军以后,我有这个筹码可以让学校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2019年,俞勇在和雷峰网交流时这样说道。
确实,正是俞勇心中的这颗火苗被不断点燃,才有了本节开头的事情:俞勇如愿成立了ACM班,此后二十年间,培养了戴文渊、李沐、陈天奇、李磊、郑曌等一大批人工智能领域大神级人物。
当然,从这里走出也不止有“人工智能大师”。2018年,一名ACM班的2004级学生在辗转多年后,终于成了哈佛医学院的教师;
而在学术研究之外,ACM学生还参与创立了一批知名公司,包括饿了么、依图科技、第四范式、森亿智能、流利说、触宝科技......
而这正源自于ACM班独特的文化。
无论是林晨曦经常提在嘴边的“敢于想象”,还是陆靖领悟到的“团队合作”,都是ACM班文化的一部分。
但对俞勇来说,ACM班文化的核心是“超越”:他希望以ACM竞赛为契机,探索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让一群有天分的少年实现“超越”。
不仅在大学的时候能取得好的成绩,更要让他们在更长的人生中,走得更远、更稳。
正如古人云: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深谙此道的俞勇,对于学生的要求远不止于专业课,尽管他在为ACM班寻找最优秀的授课教师上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
在他看来,学好专业课是一个学生的本能,一定会重视,而专业外的能力,对他们来说这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
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俞勇本人唯一负责、ACM班独有的课程“学子讲坛”上:在这门课程中,俞勇不是绝对的主导者,每一名学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内容方面,讲的则是非计算机类的文学时政方方面面。课程分四学期,每名学生一学期讲一次,主题素材均自定。
这门课程尽管不是专业课,但和雷峰网交流的多位ACM班学生们均表示,如果要选一门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课程,那绝对是“学子讲坛”。
另一门类似的课程是“教学实践”。这是一门必修课,每个ACM班的学生,都需要在本科四年里完成至少一次低年级的课程助教。通过高年级学长与低年级新人的互动,将ACM班的传统一代代传下去,形成良性循环。
如此种种,不仅让学生们理解了梦想与追求、责任与担当、感恩与包容,更是从一支冠军队开始,铸造了ACM班这个真正优秀的团队。
知行合一:
Always Challenge Miracles
2002年,是俞勇成就师者理想的转折点。这一年,戴文渊站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公开报道显示,戴文渊当时就读于苏州中学,很早就凭借竞赛获得了选择国内任意一所高校的保送资格,原本是有机会去清华的。但选清华无法保证专业,而戴文渊一心梦想着去读计算机专业,去代表中国参加世界信息学竞赛。 恰在此时,正在筹办首届ACM班的俞勇关注到这个不可多得的苗子。俞勇没找到戴文渊的联系方式,就朝苏州中学打去电话,托其转告戴文渊。 苏州中学也十分配合,成就了戴文渊和俞勇后来的故事。 虽然在中国,清北似乎总是要比其它学校高一个台阶,但在戴文渊看来,追逐自己的梦想更为重要。他接受了俞勇的邀请,成为交大第一届ACM班里最闪耀的星。 2005年,戴文渊代表交大带队参加ACM-ICPC,并夺得世界冠军。而这,距离交大上次夺冠仅仅时隔三年,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ACM班的成功,戴文渊亦因此一战成名。

戴文渊
四年后,百度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他加入百度,参与凤巢的建设。
关于凤巢的一些往事, 《中国广告引擎简史》 中我们已经分享过很多细节。
总之,对于当时的百度而言,凤巢是重中之重。
ACM班的宗旨是“培养计算机科学家”,但这里不少学生对于个人未来似乎都有着自己判断:有人想早早在社会建一番成绩,有人想放弃科研转而创业。
这本来都没有什么错误,但大部分学生对于人生长久追逐的目标并不十分明确,或者他们的判断尚属短期内的想法。 戴文渊的师弟、07ACM班的罗宇龙还记得,当他鼓起勇气来到俞勇办公室,说出“放弃直研,选择创业”的想法时。俞勇当场发火,认为这简直是对ACM班「培养计算机科学家」这个教育目标的叛离。 至少,结束研究生生涯后,创业才是被考虑的事情,否则这简直就是对优质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罗宇龙当场没忍住就哭了,但他最终还是参与到创业浪潮。 几年后,饿了么横扫中国外卖市场,创始团队之一的罗宇龙也已成为饿了么资深副总裁。 但回想起当初,罗宇龙依然会感到愧疚,觉得很对不起俞老师。 俞勇并非希望学生永远待在象牙塔,更非反对创业。但他主张学生在想不清楚以后的人生时,能够继续深造,至少不是草草将个人的学生生涯终止于本科阶段。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能经受住“老师当场发火”考验的理想,自然不是一拍脑门,而是深思熟虑的人生长期目标,日后不管遇到多少困难,也能坚定地走下去。 知行合一、追求卓越,这也是他们后来成功的重要原因。 和罗宇龙相比,戴文渊选择百度时已然在读博阶段,而他的创业则还要等到几年后功成名就时。 戴文渊没有选择谷歌、微软,这些当时顶尖人才最向往的地方,而是挑了百度。 初到百度时,戴文渊的团队一共只有三个人。所幸,他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很快成了为百度业绩最好的团队,为百度创造了最大的收入。 注重商业化的百度一旦看到效益,就会为之不断投入资源,戴文渊的团队从几个人膨胀到百余人。一位参与其中的人士告诉雷峰网,等到戴文渊离开时,仅仅直接管理的员工已经超过100,如果再加上其它配合团队,足足有四五百人。 2011年,因为凤巢的成功,戴文渊获得最佳百度人的称号。 2012年,陈雨强加入百度。戴文渊曾是陈雨强在ACM班时的“小导师”,2005年陈雨强入学时,戴文渊为交大捧回第二座ACM-ICPC世界冠军奖杯。 在陈雨强加入的时候,戴文渊和他的团队已经有了转向深度学习的想法。 不同于五六年前,深度学习虽有理论,但落地并不现实。 2012年,深度学习已经逐渐接近成熟,百度正在从逻辑回归转向深度学习的方向。 陈雨强、陈世熹这些人的加入则为百度深度学习的搭建添上了一剂催化剂,帮助百度凤巢搭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商用的深度学习系统。 在百度功成名就以后,戴文渊悄然离去,转去华为,担任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科学家。 据此前报道,戴文渊选择华为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学习做企业服务,为后来的创业做积累。 一年后,戴文渊离开华为,创办了如今业内熟知的第四范式(这一名字来自图灵奖获得者、前微软技术院士Jim Gary,2007年1月他驾船在海上失踪前的最后一次演讲正是关于“第四范式”,即密集数据驱动的科学发现。)。 而陈雨强,几乎和戴文渊同时离开百度。戴文渊在华为时,陈雨强去字节帮助其打造了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系统。 (这里预告下,关于陈雨强、刘小兵等人如何打造字节这座商业帝国,雷峰网近期将另撰文《是谁在让巨量引擎赚钱?》,请持续关注。欢迎各位读者添加作者微信Congc_a,多多交流。) 一年后,应戴文渊之邀,陈雨强同这位师兄重逢,参与到第四范式的创业。 几年后,戴文渊又找到他的师弟郑曌,邀其加入。 天才聚集的ACM班,郑曌也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2010年,正是郑曌带队捧回属于交大第三个ACM-ICPC世界冠军。 而后,郑曌在谷歌工作多年。 2017年夏天,郑曌正在Pinterest折腾个性化搜索和推荐系统的重构。戴文渊递来橄榄枝,慎重考虑后,回国参与到第四范式的工作。 作为第一代ACM班的一颗明星,戴文渊身边聚集了不少天才少年:陈雨强、郑曌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人都成为第四范式发展的源源动力。
突破创新:
星光熠熠的天才班
戴文渊固然是2002级ACM班上最耀眼的学生之一,但ACM这个天才少年班,注定不止一颗闪闪发光的星。 2002级的ACM班里,班长胡哲人是第一个IPO成功的,他创立的流利说当年红极一时。 而论学术研究,获得ACL 2021最佳论文的李磊或许又当仁不让。交大的学生时代,李磊就是班上成绩最好的,总分几乎一直都是班里第一名。 李磊
李磊也是计算机竞赛出身,ACM队以及ACM班的成立给了他进入交大的契机:当年,他通过林晨曦将申请材料转交给俞勇,才有了后面的机会。
李磊最为外人熟知的是字节的五年时间。也就是2016年,李磊从美国归来,加入字节跳动AI实验室。
不过,李磊始终是心系学术研究的。
2021年,他选择结束五年的字节生涯,重新回到美国,入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担任助理教授。
不同于戴文渊的创业追求,尽管李磊曾先后任职于百度、字节等公司。但即使在这些企业里,李磊也主要负责学术研究。
李磊在2004年进入APEX LAB。也是这个时候,他开始考虑之后的规划:要不要读博,要不要去国外等等。
他找林晨曦求教,林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一定要,因为如果你要学武功,那你一定要去少林寺,去世界上第一流的地方看看高手们是如何过招的。”
就这样,李磊下定决心去申请国外名校,也终得偿所愿。
几年后,从上海出发,李磊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始国外的求学生涯。他先是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CMU)的博士学位,毕业后还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研究员。
2014年,李磊结束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年博士后研究生涯,加盟百度美国研究院。
说来有趣,ACM班的很多学生,都曾成为百度的贡献者。这或许和百度早些年无可争议的技术文化有着不小的关系。
除了戴文渊、李磊这些第一批ACM班学生,后来的几届学生,不少也都曾是百度技术的骨干力量。
2004级学生李沐是其中之一。
也是巧合,李沐有过两段短暂的百度经历,其一是2011年4月到2012年8月;其二是2014年4月到2015年12月,正好分别对应戴文渊和李磊的百度时段。
这个圈子,说到底大家还是都没有走远。
在ACM班上,李沐被同学们称为“沐哥”。他的室友李佐凡在回忆中曾这样描述,“沐哥这一绰号从大一开始就有,估计是因为他那股领袖气场难以压制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让人不禁仰视。”
到了大三大四,李沐更是成为班上核心班干部:班长、团支书。看似吊儿郎当,实则粗中有细,重大事情上从不含糊。
这种性格直到多年后,似乎仍然不减。
2015年的最后一天,李沐在朋友圈自嘲:「15 年混迹于全球最大男性交友网站(GitHub),一切事都凭兴趣」。
过后,李沐在 CMU 机房完成了“跨年”这一盛大仪式。
时间的指针向前拨四年,李沐正在百度担任高级研究员,他为百度创建了一套分布式机器学习广告系统。
在余凯和张潼的推荐下,李沐收到CMU的offer,遂赴美深造。在CMU,李沐师从机器学习大师Alex Smola和分布式系统教授Dave Andersen。
这一次,他的搭档是陈天奇,后者是李沐的师弟。
跟李沐一样的是,陈天奇从交大毕业后,也选择了留学美国,只不过他选择的是华盛顿大学(UW)。
当时,陈天奇同时拿到UW和CMU的offer。
在CMU拜访学习时,陈天奇见到了他当时还拜为大神的李沐,李沐感叹,“现在正是大数据大火的时候,但是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不知道时代会是如何,不过反过来说,总可以去做更重要的东西。”
这也为二人之后的合作埋下伏笔。
戏剧性的是,陈天奇虽然选择了UW,但后来最终还是成了CMU的助理教授。
话说回去,陈天奇也是深度学习领域的顶级人才。陈天奇在大三时进入交大APEX实验室,跟随戴文渊研究机器学习。不过,彼时的他只是觉得“高大上”,故而选择了这门学科。
而在几年后,他终于越来越痴迷其中,成为拓荒者之一。
等到华盛顿大学时期,他醉心研究的XGBoost受到业内高度评价。作为梯度提升树模型的极致实现,XGBoost具有极强的预测能力、极高的运行效率。不仅被应用于学术界,在工业界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而这,也是后来李沐、陈天奇及另一位ACM班校友王敏捷共同创造MXNet的基础。
(在深度学习崛起之时,李沐、陈天奇及贾扬清等一批先行者以及百度为代表的国内公司率先进入深度学习框架研究,雷峰网后续计划另撰文《纯粹与不凡:AI框架的中国先行者们》,请持续关注。欢迎各位读者添加作者微信ExperienceMachine,多多交流。)
王敏捷回忆,2014年在Denver,他和李沐、陈天奇三位ACM班的学生在OSDI开会,聊到各自的研究,李沐的专业领域在于多机分布式训练,陈天奇的CXXNet包含了高效而丰富的算子库,王敏捷的Minerva能令多GPU的训练加速。三个人共同的思想是如何设计更好的深度学习系统,而各自的项目和专业领域正好互补。
于是MXNet应运而生。MXNet的名字取自Minerva和CXXNet的结合,
MXNet的项目,从零到1,仅仅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做出了完整的架构。
陈天奇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了齐心协力带来的创造力。他开始理解,研究的乐趣不光是发表论文,还是可以给别人带来什么。或者,更大胆地说,如何一起改变世界。
MXNet是深度学习代最主流的开源代码之一,被亚马逊选为AWS深度学习基础,同谷歌TensorFlow、Meta(Facebook)的PyTorch齐名。
知乎上,李沐把机器学习的发展历史写成一篇武侠小传,将修真世界里的MXNet比喻为「散修小团体」,而 TensorFlow 则是「最大流派平台」。
这是独属于李沐的文艺,也是独属于ACM班的气息。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流派天才;他们的学识,丰富而多采,方有了这番充满天马行空式想象力的描述和记录。
李磊
李磊也是计算机竞赛出身,ACM队以及ACM班的成立给了他进入交大的契机:当年,他通过林晨曦将申请材料转交给俞勇,才有了后面的机会。
李磊最为外人熟知的是字节的五年时间。也就是2016年,李磊从美国归来,加入字节跳动AI实验室。
不过,李磊始终是心系学术研究的。
2021年,他选择结束五年的字节生涯,重新回到美国,入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担任助理教授。
不同于戴文渊的创业追求,尽管李磊曾先后任职于百度、字节等公司。但即使在这些企业里,李磊也主要负责学术研究。
李磊在2004年进入APEX LAB。也是这个时候,他开始考虑之后的规划:要不要读博,要不要去国外等等。
他找林晨曦求教,林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一定要,因为如果你要学武功,那你一定要去少林寺,去世界上第一流的地方看看高手们是如何过招的。”
就这样,李磊下定决心去申请国外名校,也终得偿所愿。
几年后,从上海出发,李磊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始国外的求学生涯。他先是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CMU)的博士学位,毕业后还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研究员。
2014年,李磊结束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年博士后研究生涯,加盟百度美国研究院。
说来有趣,ACM班的很多学生,都曾成为百度的贡献者。这或许和百度早些年无可争议的技术文化有着不小的关系。
除了戴文渊、李磊这些第一批ACM班学生,后来的几届学生,不少也都曾是百度技术的骨干力量。
2004级学生李沐是其中之一。
也是巧合,李沐有过两段短暂的百度经历,其一是2011年4月到2012年8月;其二是2014年4月到2015年12月,正好分别对应戴文渊和李磊的百度时段。
这个圈子,说到底大家还是都没有走远。
在ACM班上,李沐被同学们称为“沐哥”。他的室友李佐凡在回忆中曾这样描述,“沐哥这一绰号从大一开始就有,估计是因为他那股领袖气场难以压制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让人不禁仰视。”
到了大三大四,李沐更是成为班上核心班干部:班长、团支书。看似吊儿郎当,实则粗中有细,重大事情上从不含糊。
这种性格直到多年后,似乎仍然不减。
2015年的最后一天,李沐在朋友圈自嘲:「15 年混迹于全球最大男性交友网站(GitHub),一切事都凭兴趣」。
过后,李沐在 CMU 机房完成了“跨年”这一盛大仪式。
时间的指针向前拨四年,李沐正在百度担任高级研究员,他为百度创建了一套分布式机器学习广告系统。
在余凯和张潼的推荐下,李沐收到CMU的offer,遂赴美深造。在CMU,李沐师从机器学习大师Alex Smola和分布式系统教授Dave Andersen。
这一次,他的搭档是陈天奇,后者是李沐的师弟。
跟李沐一样的是,陈天奇从交大毕业后,也选择了留学美国,只不过他选择的是华盛顿大学(UW)。
当时,陈天奇同时拿到UW和CMU的offer。
在CMU拜访学习时,陈天奇见到了他当时还拜为大神的李沐,李沐感叹,“现在正是大数据大火的时候,但是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不知道时代会是如何,不过反过来说,总可以去做更重要的东西。”
这也为二人之后的合作埋下伏笔。
戏剧性的是,陈天奇虽然选择了UW,但后来最终还是成了CMU的助理教授。
话说回去,陈天奇也是深度学习领域的顶级人才。陈天奇在大三时进入交大APEX实验室,跟随戴文渊研究机器学习。不过,彼时的他只是觉得“高大上”,故而选择了这门学科。
而在几年后,他终于越来越痴迷其中,成为拓荒者之一。
等到华盛顿大学时期,他醉心研究的XGBoost受到业内高度评价。作为梯度提升树模型的极致实现,XGBoost具有极强的预测能力、极高的运行效率。不仅被应用于学术界,在工业界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而这,也是后来李沐、陈天奇及另一位ACM班校友王敏捷共同创造MXNet的基础。
(在深度学习崛起之时,李沐、陈天奇及贾扬清等一批先行者以及百度为代表的国内公司率先进入深度学习框架研究,雷峰网后续计划另撰文《纯粹与不凡:AI框架的中国先行者们》,请持续关注。欢迎各位读者添加作者微信ExperienceMachine,多多交流。)
王敏捷回忆,2014年在Denver,他和李沐、陈天奇三位ACM班的学生在OSDI开会,聊到各自的研究,李沐的专业领域在于多机分布式训练,陈天奇的CXXNet包含了高效而丰富的算子库,王敏捷的Minerva能令多GPU的训练加速。三个人共同的思想是如何设计更好的深度学习系统,而各自的项目和专业领域正好互补。
于是MXNet应运而生。MXNet的名字取自Minerva和CXXNet的结合,
MXNet的项目,从零到1,仅仅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做出了完整的架构。
陈天奇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了齐心协力带来的创造力。他开始理解,研究的乐趣不光是发表论文,还是可以给别人带来什么。或者,更大胆地说,如何一起改变世界。
MXNet是深度学习代最主流的开源代码之一,被亚马逊选为AWS深度学习基础,同谷歌TensorFlow、Meta(Facebook)的PyTorch齐名。
知乎上,李沐把机器学习的发展历史写成一篇武侠小传,将修真世界里的MXNet比喻为「散修小团体」,而 TensorFlow 则是「最大流派平台」。
这是独属于李沐的文艺,也是独属于ACM班的气息。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流派天才;他们的学识,丰富而多采,方有了这番充满天马行空式想象力的描述和记录。
薪火相传:
永不停歇地前进的伯禹
因为一众ACM班学子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杰出成绩,ACM班开始被冠以“人工智能的摇篮”。 但俞勇并不仅仅这样想,他觉得教育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现在即便不是人工智能兴起,其他的新兴领域,ACM班的学生照样还是可以崭露头角。 能够有这样的自信,远不止于交大对学生在计算机教育或者专业技能的培养,更重要的可能是其它一些看上去不那么重要的软实力,比如人文素质的培养。这使得ACM的学生不仅有能力,也有自主开拓新领域的意识。 很多年轻人可能给自己打上标签,但俞勇一直跟学生强调的一点是,不要给自己打标签。现在不感兴趣的东西在未来某一天也可能会沉迷其中,这使得ACM班的学生有了更多无限可能。 在跟雷峰网的交流过程中,俞勇不断地在强调这一点。 “我不是希望能够把他们脑袋装满,我确实希望他们能够有好奇心。所以,我们不是专门为了人工智能,也许有新的东西,我们班级的学生照样可以成为另一个黄埔军校。” 在这一点上,俞勇显示出无比自信的神态。而在和ACM班的学生交流中,我们更进一步体会到俞勇自信的底气。 李磊在一次与雷峰网的交流中也提到,他ACM班的同学们不仅仅是计算机竞赛出身,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竞赛和在校选拔出的佼佼者。在计算机方向的ACM班,很多人仍然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在他看来,ACM班打下的基础让他们无论选择哪个方向都容易做出成就,“只不过我们大多数人恰好选择了计算机而已。” 这些人敢于尝试新的东西,并为之痴迷。 的确,ACM班的培养从来不止有计算机,他们甚至有学子讲坛这样的看起来像个“文科专业课”一样的科目。 俞勇不希望,让学生在学校里学到所有的东西。当然,他可能也做不到。但正是这种巧妙的留白,给了这些学子更多可能性。 他们自由,他们勇敢,他们努力。 他们亲历了中国计算机科学的一次伟大教育实验,而他们的参与和探索也为后来中国特色的计算机教育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才有了如今:这些ACM班学生像群星一样,闪耀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对已经执教30余年的俞勇而言,他还有很多工作,比如,将在ACM班积累的经验推而广之。 在一次次的对外交流中,俞勇深切感受到过外界学子的热情,这让他萌生了创办一所教育学校的想法。 2018年,人工智能课程开始进入高中,俞勇原本准备退休以后办学校的计划被提前数年。 思考清楚以后,俞勇向学校领导说明想法。和当初创立ACM班一样,俞勇再次得到肯定的回复。前提是:不能丢掉ACM班的教学。 ACM班是俞勇在交大交出的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而交大也给了俞勇足够的信任和宽容。 正因如此,俞勇能够自由地在交大,乃至整个上海范围内寻求名师。比如,俞勇请来了复旦大学的朱洪负责算法教学。后者不仅是上海,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是享有盛誉的。 相比起ACM班,俞勇的新项目伯禹教育更像是他的个人理想,与交大不能说绝无交集,但也相去甚远。伯禹面向的不再是交大学生,而是全国所有愿意学习人工智能计算机的学生。 但在“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这一指导思想上,伯禹教育和ACM班别无二致。 俞勇关于伯禹教育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1世纪的前十年。 彼时,俞勇还是主管教学的系主任,本硕博的学生都归俞勇管理,因此跟大部分学生关系都比较亲近要好,他始终站在学生的角度,尽其所能的满足学生诉求。 比如,当时本科生最关键的有一个阶段是直升。由于学校给每个专业的直升比例是一样的,不可能变多。为了让更多学生得到机会和资格,俞勇创造性地想到了和国内其他学校进行同等交换。 简言之,彼时,很多高校都有直升,本校和外校各有一定比例。俞勇通过和复旦、浙大等学校进行交换,满足了不少学生直升的诉求,帮助他们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很多学生毕业后,对俞勇仍然念念不忘。教过那么多学生的俞勇,很难对每一个学生始终记忆犹新,但他们几乎都始终铭记着俞勇。 有一年俞勇去美国碰到一个学生,他已经记不清。这位学生就拿出,毕业跟俞勇的合影,激动地说道,“这个可以证明我是您的学生。” 他和这些毕业生的联系远远不止于此。一名毕业工作于青岛海洋大学的交大毕业生,多次邀请俞勇去青岛为当地学生讲课、交流。三番五次得到邀请的俞勇终于无法拒绝。 正是这次交流,让俞勇感受到全国教育资源的差距。俞勇讲一个小时,但是可能两个小时都难以脱身,学生问题多如牛毛,“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都很迷茫。”俞勇这样感叹。 从那以后,凡有时间,俞勇对于各种邀请几乎来者不拒。这些学校有的可能是三流大学、甚至专科学校,再到后来的中小学,俞勇只要能排开档期,都尽量去参加。 这样的一次次经历,让俞勇感受到肩上更大的责任, “我的确属于交大,但我想我还是应该属于社会。” 俞勇的教师情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无数学子,其中不乏回归交大与伯禹,同恩师再重逢的天才少年。 2016年,从英国伦敦大学(UCL)博士毕业的张伟楠,选择归国,和俞勇一样,成为交大一名老师。 张伟楠
UCL时期,张伟楠师从数据科学大师汪军教授,在机器学习和和数据发掘领域取得不俗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变分法计算广告出价优化体系。
“当时的生活是,白天做谷歌的研究课题,晚上回到家或者周末的时候就做数据科学算法的研究、参加世界范围的数据挖掘比赛。”张伟楠和雷峰网这样回忆当初的生活。
而张伟楠一名UCL时期的同学张长旺对其评价道,“当时,伟楠每天在实验室里面经常走得很晚,是泡在实验室里面的一批人。”
几年后博士毕业,张伟楠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归国,加入上海交大,成为和俞勇一样的师者。
在张长旺看来,张伟楠回来选择交大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他在很多大公司实习过,知道公司里面实际是什么情况,对学校了解的更是不必多说,伟楠对未来规划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这也正符合俞勇对学生的培养方向,比起专业,俞勇更希望这些学生对未来有一个清晰认知,早早确立好自己的人生目标。
俞勇还在不停歇地走在教育路上,而他的学生们也已然开始成为传道者。
伯禹教育的推动者之一张惠楚是一名妥妥的90后,也是ACM班的毕业生。
1994年出生的张惠楚在来到交大以前,一路顺风顺水。然而,来到交大以后,身边个个学霸的他压力骤增,一度自暴自弃,成绩直线下滑。
直到大三,张惠楚重新起航,一路读到交大博士,期间还远赴康奈尔大学交流学习。
毕业后,受恩师俞勇的邀请,成为伯禹教育的推动者。
类似和俞勇一起,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事业的学生,还有很多。
甚至在对ACM班“继任者”的问题上,俞勇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希望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学生,而且要对教育有情怀。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培养出好学生。”
而且,俞勇希望这位继任者在班级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舍个人而取班级。只有如此,ACM班和它的精神才能不断地延续。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俞勇培养了一群天才少年,他们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又始终在传承着ACM班的精神。
俞勇还行走在教育大道上,他期盼为交大,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天才,他和天才的故事还在继续。
张伟楠
UCL时期,张伟楠师从数据科学大师汪军教授,在机器学习和和数据发掘领域取得不俗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变分法计算广告出价优化体系。
“当时的生活是,白天做谷歌的研究课题,晚上回到家或者周末的时候就做数据科学算法的研究、参加世界范围的数据挖掘比赛。”张伟楠和雷峰网这样回忆当初的生活。
而张伟楠一名UCL时期的同学张长旺对其评价道,“当时,伟楠每天在实验室里面经常走得很晚,是泡在实验室里面的一批人。”
几年后博士毕业,张伟楠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归国,加入上海交大,成为和俞勇一样的师者。
在张长旺看来,张伟楠回来选择交大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他在很多大公司实习过,知道公司里面实际是什么情况,对学校了解的更是不必多说,伟楠对未来规划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这也正符合俞勇对学生的培养方向,比起专业,俞勇更希望这些学生对未来有一个清晰认知,早早确立好自己的人生目标。
俞勇还在不停歇地走在教育路上,而他的学生们也已然开始成为传道者。
伯禹教育的推动者之一张惠楚是一名妥妥的90后,也是ACM班的毕业生。
1994年出生的张惠楚在来到交大以前,一路顺风顺水。然而,来到交大以后,身边个个学霸的他压力骤增,一度自暴自弃,成绩直线下滑。
直到大三,张惠楚重新起航,一路读到交大博士,期间还远赴康奈尔大学交流学习。
毕业后,受恩师俞勇的邀请,成为伯禹教育的推动者。
类似和俞勇一起,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事业的学生,还有很多。
甚至在对ACM班“继任者”的问题上,俞勇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希望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学生,而且要对教育有情怀。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培养出好学生。”
而且,俞勇希望这位继任者在班级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舍个人而取班级。只有如此,ACM班和它的精神才能不断地延续。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俞勇培养了一群天才少年,他们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又始终在传承着ACM班的精神。
俞勇还行走在教育大道上,他期盼为交大,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天才,他和天才的故事还在继续。
携手·超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俞老师太难了。” 在与ACM班的校友交流的过程中,雷峰网不止一次听到这句话。 2012年,在ACM 班十周年的纪念文集《携手》一书中,俞勇曾这样写道: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叹息:现在的学生没有追求,缺乏理想,更缺少激情。我的回答:错!他们恰恰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代,只是我们读不懂他们,更少有人去研究如何读懂他们。 二十年前最初创办ACM班的时候,俞勇遇到的主要困难,在于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摸索“如何读懂他们”,并激发他们的理想与激情。 这一点,从ACM班早期的课程和教学计划的不断调整可见一斑。 随着时间和经验的沉淀,俞勇所考虑的问题,也更多转向了ACM班精神的传承上。 上海交大执教的近三十年间,俞勇见证了诸多实验试点班级的演化:从最早的试点班,到后来90年代成立的教改联读班,之后又变成了理科实验班(之后在此基本上成立了致远学院)——虽然这些变化都能给上海交大的优秀学生培养带来了新的机会,但也同时给这些毕业生带来一些不适感。 在俞勇看来,一个班级一旦成立,就一定要想清楚,而非一蹴而就,等到有了新思路再随意更换。他始终从学生角度出发,为学生考虑。“成立一个班级很容易,但是在考虑其必要性的同时还要考虑其可持续性。” 俞勇还记得,几年前的一次校庆活动上,联读班已经没有了,一些学生回到学校后无人接待的场景。俞勇告诉他们。“你们还可以找俞老师呀,你们还是计算机系的学生。” 正因如此,俞勇更看重ACM班的可持续发展——ACM班是以ACM-ICPC冠军为契机建立的,在第一个十年里,ACM班三次夺得ACM-ICPC冠军,在竞赛人才培养上证明了自己。 但在第二个十年,俞勇需要面临的问题更多也更复杂。教育资源的集中化,使得交大更难争取到最优秀的竞赛生;除了竞赛之外,ACM班还需要在其他领域(例如说科学家培养)也能交出同样优秀的成绩单。 第二个十年中,我们看到了ACM班的可喜变化:John Hopcroft等强援加盟上海交大,使得ACM班变得更加国际化;而ACM班的毕业生也陆续成长起来,目前已有30多位ACM班校友获得海内外教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为期,ACM班还需要更多的十年,去探索新的领域。 2021年,俞勇和雷峰网的一次交流中透露,2022年ACM班20周年活动的主题将会是“超越”。这是因为ACM 班的班训是“携手.超越”,不仅要携手共同进步,更要让学生自我觉察人生志趣并将其实现,在将来一同改变世界。 回首ACM班的前二十年,这不仅是学生相互间的携手与超越,更是俞勇与学生们的携手与超越。 正如俞勇对雷峰网说过的一句话: “培养图灵奖得主是我的梦想,也许永远实现不了,但是我享受能不断地遇见不一样的自己。”整理不易, 点 赞 三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