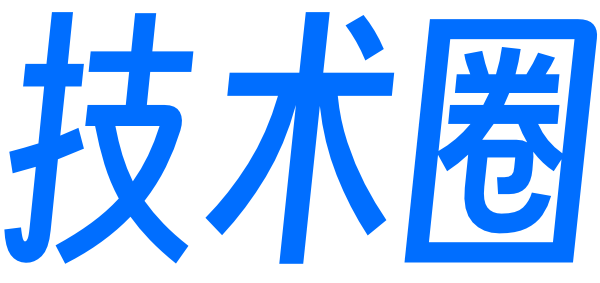施一公:年轻人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
日期 : 2021年03月04日
正文共 :2970字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拿到offer后争取更好待遇的重要性,但普林斯顿大学是我梦幻中的学术圣地,怎能在这种地方讨价还价呢?!这是我的性格。更何况,拿到这个offer实在是惊喜,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工作面试,事先是做好了失败准备的!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1997年共有两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位置,但却有四百多名年轻的博士后科学家申请。经过层层筛选,确定了六个面试人。我作为六人中的一员在2月27日最后一个到普林斯顿面试。去世界著名的普林斯顿,心情既紧张又激动,26日一晚上基本没能睡着,脑子里一遍遍地全是精心准备的介绍我的科研进展的幻灯片。早晨6点起床,赶上了七点从纽约Penn Station开往南方的火车,七点五十抵达普林斯顿。九点整开始面试。
27日上午分别与四位教授举行一对一的每人45分钟面谈,其中一人是2001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Shirley Tilghman。因为我已经对他们的科研事先有所了解,所以面谈还算顺利;但Shirley在认真讲述了她的科研进展后很意外地考了我一个相关问题,我极为紧张地思考后做了还算得体的回答,她点头称对,我才收了一身冷汗。中午与几位博士生一起午餐。下午一点半午餐后,又与三位教授进行面谈,其中第一位是时任系主任的Tom Shenk,第二位是前系主任、后曾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Arnold Levine。下午4点整,我在系报告厅LTL003给了50分钟的学术报告。我发挥得很好,效果出乎自己的意料,回答问题时已经完全自信。原定晚餐由Tom Silhavy及另外两名教授参加;我的学术报告后Tom Shenk和Arnold Levine两位重量级教授临时决定共进晚餐,而且Shenk很有暗示意味地对我说,“I think you will become a superstar at Princeton.”
晚餐安排在普林斯顿小城著名的法国餐馆Lahiere’s Restaurant。Levine介绍说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22年中最喜欢的餐馆;Shenk则指着一张爱因斯坦挂像下面的桌子说,“In a few years, if I invite you to dine at that table, then you will soon receive tenure at Princeton.”晚餐聊得很开心,根本不象是面试的一个环节。当天晚上我下榻Nassau Inn,由于白天面试的顺利进行,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直到凌晨4点多才入睡。第二天继续与8位教授的一对一面谈,包括后来接Shenk做系主任的Lynn Enquist和199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Eric Wieschaus。由于连续两天没休息好,午餐后我已经筋疲力尽,居然在与Wieschaus面谈时差点打盹,害得我红着脸坦白没有休息好。面试直到28日下午4点结束,也结束了持续整整两天的面试。老实说,第二天的感觉远不如第一天,心里也有点儿忐忑不安。还好,最终拿到了offer。
Shenk和Levine对我各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至今想与每一位年轻PI分享的忠告。和每一位刚刚开始独立实验室的助理教授一样,我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申请到科研基金,尤其是NIH的项目经费;这种担心对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尤其真实和迫切。1998年1月,初到普林斯顿,我对Shenk表达了这种担心;Shenk回答道,“Yigong,please focus on your research and apply for NIH grants only when you have significant preliminary results. If you fail to obtain any external funding but are doing fantastic research, we will support you! Please don’t worry.”Shenk的这句话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只要我的科研出色,即使拿不到外面的经费,系里也会支持我!
不可否认,每一位助理教授都对能否拿到tenure耿耿于怀;我也一样,从在普林斯顿正式报到的第一天起,就常常想这个问题,而且常常想得很紧张。在1991至1997的六年中,七位年轻的助理教授试图在分子生物学系拿到tenure;可惜,只有一位成功,其他六人都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另谋它职。Levine看透了我的担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Yigong, think about it: getting tenure is not so difficult. If you can reproduce your track record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a postdoc in the next 5 years, you will get your tenure at Princeton or any other top-notch university in the US.”
Levine又对我做独立PI提出了具体建议,“Treat yourself as a super-postdoc in the lab during the first 3 years. You must work on your own projects at the bench and supervise your students. This way, you will get your research take off immediately.”我完全接受Levine的建议,不仅天天在实验台上做自己的课题、还尽全力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做研究,科研工作很快形成局面,仅用三年就顺利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庆祝我顺利tenure的party上,Levine又一次忠告我,“I know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on the bench for 3 years. Now your lab is fully established, and you need to shift your focus from bench work to supervision. Some people believe, and I agree, that spend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your time on the bench work after being a PI for 5 years won’t make you fantastically successful.” 当时对这条建议我从心里有点不认同,但回望过去十几年的科研经历,这个建议是很有道理的。
我还告诫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包括一些他拉过关系、关照过他的人)从心里看不起。在学术界,这永远是真理!在美国是,在中国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
与所有的年轻PI共勉!
— THE END —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