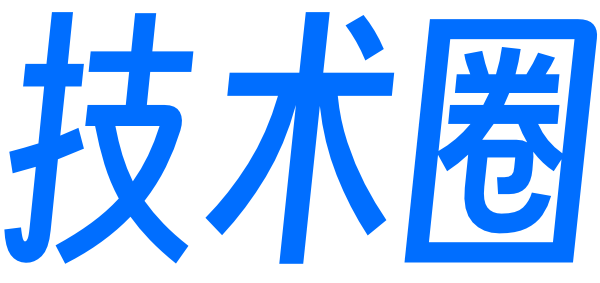技术发展史,为什么又是一部人类的恐惧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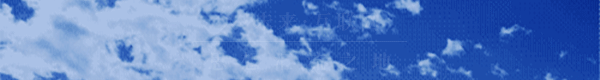

对技术的恐惧是一种社会的接纳机制,它使技术发展不会脱轨,而是在一定的规制范围内,朝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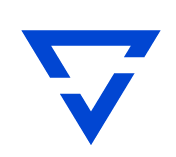
1814年11月29日凌晨,《泰晤士报》印刷车间的工人们正在焦急等待。不久前,老板约翰·沃尔特宣称,因为要等一条来自战后欧洲的最新消息,让他们先暂停印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工人们愈发担心无法准时完成当日的印刷工作。彼时,报界还都采用手工印刷机,一组熟练工人每小时可以印刷250到300张报纸。作为英国第一主流大报,《泰晤士报》每天发行5000份,需要所有印刷工不停工作两个小时。
凌晨6点,约翰·沃尔特终于走进车间,手里还拿着一份报纸。
面对吃惊的工人们,他说:
今天的《泰晤士报》已经印出来了。而这份报纸,是用在另一幢楼秘密安装的蒸汽印刷机印成的。
沃尔特之所以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是因为他之前购置的第一台蒸汽印刷机被工人捣毁了。和当时所有手工劳动者一样,印刷工人也担心机器会抢了他们的饭碗,毕竟机器印刷机每小时能印1100份报纸,是手工印刷机的4倍。
这个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此时英国工业革命肇兴,蒸汽机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导致大批工人失业、破产。对机器的抵制情绪在全社会范围内蔓延开来,引发大规模破坏行动。1779年,英国莱斯特郡一位名为奈德·卢德的工人,牵头捣毁了工厂的织袜机,而后数年,整个英国掀起了一场捣毁机器的工人运动,也被称为“卢德运动”。
随着当局镇压与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工人们与机器被迫达成了一种共处关系,卢德运动成为一段历史,而“卢德分子”也逐渐被视作落后、愚昧、抵抗新技术的象征。
问题是,卢德分子似乎从未在技术发展史中消失。站在当下回望,技术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个吊诡的“规律”:当新技术出现后,人们总是会心怀抵制情绪。这种情绪有时体现为整体性的担忧与恐惧,有时则表征为批评、质疑等具体化行动。
我比较多关注媒介技术史。在这段历史中,卢德分子的“还魂”尤为明显。从书籍、报纸等文字媒介,到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再到互联网和算法,每一代新媒介的产生与发展,无不伴以负面的牵扯。更奇怪的是,当更新一代的媒介面世时,旧媒介摇身一变,反而会成为“良善”的代表。
循着这个思路,本文意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当新技术涌现而出,我们为何总是首先会以害怕、担忧等抵制情绪来面对?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新技术恐惧”的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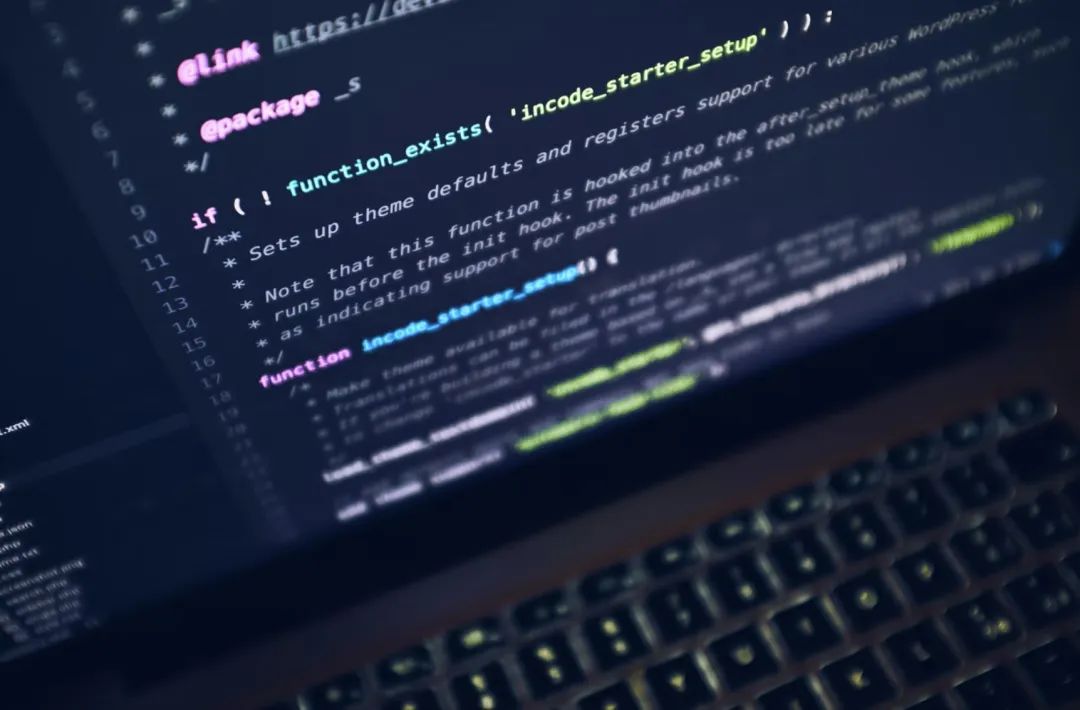
01
“恐惧”是新技术的代名词

文字媒介,或者说书写媒介,在当下被视为最严肃的信息渠道。如果知识获取方式也存在鄙视链,那么书籍或者文章大概率会排在鄙视链顶端。但在对技术的恐惧史中,文字媒介却首当其冲。
古希腊时期,书写媒介被视为口语文化的威胁。苏格拉底的批判最具代表性,在《斐德罗篇》中,他斥责文字,呼唤对口语的重视。苏格拉底担忧的关键点在于,文字削弱了人们大脑的功能,特别是记忆力。同时,书面文字是静态的,很容易受到误会和曲解,但又无法回应读者的提问。
考虑到彼时的文化语境,这种批评其实可以理解。口语是希腊文化的核心,不仅用于日常沟通,政治、哲学等严肃议题的交流,也通过面对面的对话和辩论来进行。使用的惯常性将口语推崇到几近神圣的地位。在古希腊学者看来,口语具有一对一、鲜活性、互动性、对等的互惠性等特点,而且因不可复制显得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人与人相遇的最高境界。
相比之下,文字则被视为“淫荡的”“不忠贞的”。因为它不区分受众与对象,具有任意撒播的特性。形式上也是单向的,书写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极为不平衡——书写者处在统治地位,而读者只能被动臣服。
如约翰·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所说,
苏格拉底们渴望一种没有主奴之分、主从之别的“忠贞爱情”,但书写只是不分对象的随意抛洒,它与接受者不可能实现真正契合。
作为书写媒介鼎盛时期的代表,报纸开启了大众传播时代,但对报纸的批评更是声量巨大。报纸以空前的速度和效率把信息供应给大众,但当时不少学者和记者批评报纸对传播速度的痴迷,牺牲了报道内容的深度性。与此同时,创建报纸的门槛和高昂费用,意味着少数人控制了信息流动,致使信息的传递愈发呈现出单向、集中的特点。

接下来的历史我们更加熟悉,在文字媒介之后,出于对传播速度与广度的追求,促生电子媒介的出现,而新兴的电子媒介很快接过了“恐惧接力棒”。比如电报,不少研究者认为它与时代性的精神紧张有关,如1881年乔治·比尔德在《美国式紧张》中指出,“电报是紧张的成因之一,而对于紧张这种病的严重性我们尚一无所知。”
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些戏谑,但看似人畜无害的电话,在发明之初也被认为是破坏家庭关系的“元凶”。1926年,旧金山的一次调查问卷中就包含这样的问题:“电话使人更活跃还是更懒惰?它是否破坏了家庭生活和探访友人的传统?”
广播、电视出现后,学者与评论家又抨击电子媒介会损害人类形成于印刷时代的、缜密理性的思维模式。其中以尼尔·波兹曼对电视的批评最有代表性,《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和《技术垄断》三部曲,每一部都是波兹曼对于电视这种“新媒介”的指责,而书写媒介的严肃地位,其实也正是在对电子媒介的批评中树立起来的。
电视之后,新技术的恐惧史还在继续。当计算机面世,很快被打造成洪水猛兽一样的可怕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声音,当属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一书中对网络导致人类思维退化、文化衰退的批判。他甚至惊悚地提出:“记忆外包,文明衰亡。”
当我们不再关注网页跳转如何损害使用者记忆,或者是手机使用如何导致时间碎片化等课题时,算法和人工智能出现了,它们构成了当下新技术恐惧的主力。
对于算法,有“信息茧房”“算法偏见”等批评,而对人工智能的批评则更加激烈,且动辄就上升到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层面。2014年,尚在世的霍金宣称:“完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种族的终结。”同年,埃隆·马斯克也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生存威胁,我们正在用人工智能召唤恶魔。”
02
我们缘何警惕新技术?

技术发展史,似乎也是一部人类的恐惧史。一个问题渐渐浮现:我们为什么对新技术如此警惕?
尽管每一轮对新技术的恐惧都有具体的动机与表象,但也能看出一些底层因素在发挥作用。
首先,人类天生恐惧未知,这是我们的祖先在野外环境生存时留下来的基因自觉。
当新技术面世,它的内在构造与运作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性,都还不为我们所知,面对不了解的事物,自然会有警惕、防备的心理。所以,新的技术在短时间内会面临来自各个领域的目光审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乐观和看好,也有一小部分是警惕性的怀疑与批判,因为绝对量够大,后一种声音也难免显得刺耳。
同时,技术的变革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迁,每一轮技术更替,都会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当旧技术造成的变化逐渐稳态化,被接纳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好不容易适应了变化的人们已经很难有心力和脑力经得起新一轮折腾。
需要承认的是,新技术带来的浪潮,必然有受益者,也必然会有被淘汰的人。所以,人们之所以会警惕新技术,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被新技术所取代。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提出“创造性毁灭”的说法,他认为,当效率更高的新技术出现后,依托旧技术的产业势必会受到冲击。比如电灯发明后,蜡烛工人就会面临失业的问题。
本文开头所讲的《泰晤士报》的故事,显示了个体对新技术的排斥有多严重,也具体呈现了这种排斥的原因:担心自己被取代。面对效率十倍于自己,并且成本更低的机器,很难有人不产生“替代焦虑”。

近年来对互联网、对人工智能的恐惧与抵制,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银行柜台的职员失业了,打字员这个行业整体消失,自动驾驶解雇了司机,机器人替代了工人,造就一大批“无灯工厂”。每一个人都会不自觉的联想,区块链、web3它们会取代什么?下一代的技术会不会取代自己?
取代不仅发生在就业方面。当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的领域被技术侵入之后,人们的焦虑和恐惧更加剧烈。人工智能研究者、《哥德尔、爱舍尔、巴赫》一书作者侯世达曾直言,自己被“音乐智能实验”(EMI,可以理解为音乐编写程序)所创作的作品吓坏了:“我厌恶它,并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人工智能对我最珍视之人性的威胁。”
侯世达所担心的是,智能、创造力、情感,甚至是意识本身——这些最为珍视的人性特征和人类精神,在AI面前不过是“一套把戏”,肤浅的暴力算法就可以将其破解。技术是人的延伸,这种延伸反过来创造了主体性焦虑。
侯世达的担忧也透露了另一种趋势,即技术正越来越多参与到思想文化领域。而大多数对于新技术的恐惧,也集中于传播信息、影响思想的技术类型,即媒介技术。
与几个世纪前的人们不同,在享受过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红利之后,我们现在对实体的机器和基建设施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崇拜的感情。而批判的矛头更多指向了数字技术,乃至更具体的媒介形式,诸如算法和短视频等等。
原因在于,媒介技术是信息流动的渠道,是用来向人们传递讯息的工具,信息的传递往往与说服、宣传甚至是操控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而人类天生对控制思想的手段存有恐惧情绪,害怕失去控制、丧失自由意志。这种恐惧表征为各种类型的丧尸电影,丧尸为人类社会植入了一种“无脑之恐惧”的隐喻,他们漫无目的的游荡形象,其实正是人们担心被技术操控后的结果。
媒介技术离人的思想如此之近,自然也就引起了更大的警惕与批判。正如在电视出现后,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将电视比作“一种有效的麻醉剂”,让人们的大脑停止运转:电视提供了“娱乐和刺激”,而除了“最低限度的注意力”外,它别无所求。
03
对技术的恐惧,是一种必要机制

经过上文的探讨,我们大抵会发现两点规律:
第一,从恐惧的主体来看,存在很明显的二元分野:大众往往是技术的享用者,而批评技术的多是专家和学者。这更像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他们认为大众是对于媒介技术毫无抵抗力的靶子,缺乏充足理性筛选信息,缺乏适当自制力抵御技术的影响。可以说,他们对技术的批判,源于对大众的担忧。
第二,历史上对新技术的恐惧是一种循环,当更新的技术出现后,对旧技术的恐惧荡然无存。我们现在已经不认为电话会破坏亲密关系,也没有人担心电视会“麻醉受众的大脑了”。这其实也好理解,在技术获得一种程度的发展,它所带来的红利开始释放,人们在更加了解它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范围之后,自然就不会再有那么深的恐惧。
那么,既然事后都被印证了无效性,对新技术的恐惧真的是不必要的杞人忧天吗?
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其实这种恐惧,正是技术发展历程中的必要一环。

新技术问世后总会有一段过渡期,这也是社会对它关注最密切的时期。在这段时期,新技术会因弥漫在社会中的恐惧情绪而遭受严厉审视、批评与指责。关键是,技术的发明者和使用者会据此制定适当的制度与规矩,而新技术会随之作出调整。
这一过渡阶段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果一项技术还正处在被讨论的风口浪尖,说明它正处于过渡期,还并不成熟。
雷蒙·威廉斯将这段过渡期看作是技术的正当化过程。他认为,任何技术都不会直接改变社会,它的社会嵌入需要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技术-文化复合体,传播技术总是先要被赋予一定的社会意义之后,才能够作为一个被驯化了的“物”进入我们的生活世界。”
可以说,对技术的恐惧是一种社会的接纳机制,它使技术发展不会脱轨,而是在一定的规制范围内,朝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演进。
电视就是一个例子。笔者曾经对深圳大学的常江老师有过一次访谈,他认为,
正是在电视面世之初,有大量反思和批判出现,并且由此带来对电视的大规模改造,才塑造了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电视。我们觉得对电视的批评是杞人忧天,是因为现在的电视已经不是当初的电视了,而是经过了反思与改造的电视。
对算法的恐惧也是,它引起了一系列对于算法的规制,从而为算法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回顾对于书写媒介、广播、电视、互联网的批评,尽管事后看起来有一些不必要,但它们或许也同样在无形中发挥了作用。不能因为现在的技术变好了,就不承认之前问题的存在,不承认之前批判的有效性。
历史映照着当下。如果从漫长的技术发展史中能够得出什么道理,或许就是:对新的技术保持一种适度质疑的精神,是每一代人应有的责任。新技术常常要承受怀疑的目光,但这种目光是必要的,技术就是在“永恒的怀疑”中越变越好。
当然,我们也应该理解技术恐惧背后的个体动机,他们或许就是在新技术的浪潮中被抛下的人们。《泰晤士报》老板沃尔特虽然下决心采用蒸汽印刷机,但他也向工人保证,他们不会因此失业或蒙受损失。一个好的社会的标志,就在于它如何帮助追赶不上技术潮流的人们找到新的出路,过上体面的生活。